試論我國民事訴訟中免證事實之應有範圍及其适用
- 綜合
- 2年前
- 232
【學科分類】民事訴訟法
【出處】《法學評論》2004年第4期
【摘要】本文依證據法之基本理論,結合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以獨特的視角對現行司法解釋中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作了全方位的檢視。本文認為,在現行民事訴訟運作模式下,惟衆所周知之事實與推定之事實始屬免證事實。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對這兩項該免證事實之适用分别作了闡析。
【關鍵詞】免證事實;辯論主義;證明力
【寫作年份】2004年
【正文】
在民事訴訟理論上,免證事實又稱不要證事實,乃指無須經由當事人兩造提供證據予以證明,而可直接由受訴法院裁判确認之事實。因現代民事訴訟皆采證據裁判主義,受訴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端以證據為基礎,故免證事實乃為證據裁判主義之例外。又因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兩造負舉證之責,故免證事實同時構成舉證責任之例外。由于免證事實攸關當事人舉證責任之界阈,關乎當事人兩造利益至巨,故各國立法例皆對免證事實予以明确界定,以杜受訴法院恣意濫用之弊。盡管我國現行民訴法并未明定哪些事實無需當事人舉證,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适用意見》)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幹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則先後對免證事實作了相對明确之界定,從而部分為民事審判實踐中受訴法院認定免證事實提供了依據。然則細細推究該兩項司法解釋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不難窺見,其存在諸多與現行立法結構和相關訴訟理論相乖悖之罅漏。舉其荦荦大者,尤以免證事實範圍之不當與适用之失範為著。是故,從理論上厘定現行法框架下免證事實之應有範圍并對其正确适用予以闡說洵屬必要。本文之寫作即是基于此一目的之考量。
一、免證事實在現行司法解釋上的體現
雖然現行民訴法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付之阙如,然《适用意見》第75條和《證據規定》第8條、第9條,則皆對免證事實之範圍作了相對明确之界定。
《适用意見》第75條規定:“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1)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和提出的訴訟請求,明确表示承認的;(2)衆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及定理;(3)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4)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實;(5)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證據規定》第8條第1、2款規定:“(第1款)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确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除外。(第2款)對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未表示承認也未否認,經審判人員充分說明并詢問後,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證據規定》第9條規定:“(第1款)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一)衆所周知的事實;(二)自然規律及定理;(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四)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認的事實;(五)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确認的事實;(六)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第2款)前款(一)、(三)、(四)、(五)、(六)項,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盡管《适用意見》第75條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依“新法優于舊法”之法律适用原則,不再具有指導民事審判實踐的效力,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在學理研究上的價值。這是因為,将最高人民法院于不同年代(《适用意見》于1992年公布,《證據規定》于2001年公布)對同一制度所作的規範予以比較考察,不僅能窺見司法解釋制定者關于此項制度适用之價值取向上的更易,從而為将來立法者之價值抉擇提供參考,并且能夠為将來的立法提供部分之實證資料,從而裨益于立法之完善。本此之旨,本文試對該兩項規範比較如下:
其一,《證據規定》第8條第1、2款分别規範了明示的自認與默示的自認,[1]并明定兩者皆為免證事實。與《适用意見》第1項相比,《證據規定》不僅增加了拟制的自認制度,從而将拟制自認之事實亦納入免證事實之範圍,并且注意到了《适用意見》第1項“一方當事人對訴訟請求的承認”在效力上與自認尚非同一,[2]并将其擯除在免證事實之外,足資認同。
其二,《證據規定》第9條一改《适用意見》第75條将“衆所周知的事實”與“自然規律及定理”并列規範之樣式,于第(二)項、第(三)項對二者予以分列誠屬妥适。這是因為“衆所周知的事實”與“自然規律及定理”從内涵上講并非同一層面之事物,将其并列從邏輯上講殊非妥當。
其三,相對于《适用意見》第75條,《證據規定》第9條增列“仲裁裁決所确認的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一。窺其緣由,我們認為可能是因為《适用意見》公布之時,仲裁尚不采一裁終局制,仲裁裁決作出後,當事人不服仍可向法院起訴,故将仲裁裁決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尚存在制度上的障礙。
其四,依《證據規定》第9條第2款可知,受訴法院關于免證事實之适用并非絕對。表現為除“自然規律及定理”外,其他各項免證事實均允許對方當事人提供相反的證據予以推翻。
盡管如此,《證據規定》與《适用意見》在免證事實範圍的界定上,從整體上看幾乎同一,這充分表明法律适用者關于免證事實應有之義的認識并未有實質性的改變,《适用意見》所存在的舛誤仍為《證據規定》所沿襲。我們認為,其根本緣由在于法律适用者對現行民事訴訟之運作模式及相關訴訟理論缺乏基本認識。在我們看來,以現行民事訴訟運作模式為斷,自認之事實并不能稱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衡諸相關訴訟理論,自然規律及定理,生效裁判所确認的事實,仲裁裁決所确認的事實,有效公證文書所确認的事實亦不能當然地作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在現行民訴法之框架下,惟衆所周知的事實與推定的事實始能成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
二、自認的事實不能作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
自認的事實之所以不能作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認乃辯論主義之産物,在采職權探知主義之我國決無适用之餘地。現代各國民事訴訟,就當事人對訴訟資料(證據資料)之提供與受訴法院認定案件事實之關系而言,殆有兩種運作模式:一日辯論主義,二日職權探知主義。辯論主義包括三層要義:其一,受訴法院不能斟酌當事人兩造未主張之事實作為判決之基礎資料;其二,對于當事人兩造之間無争執之事實(自認、拟制自認),受訴法院無需調查證據,可直接采納作為判決的基礎資料;其三,受訴法院對于當事人兩造争執之事實,應依當事人所聲明之證據予以調查。[3]而職權探知主義在内涵上與辯論主義截然相左,表現為:其一,對于當事人兩造未主張之事實,受訴法院亦可将其作為裁判的基礎;其二,對于當事人兩造之間無争執之事實,受訴法院仍需調查其真僞,而不能直接采納作為判決之基礎資料;其三,受訴法院對事實之調查不受當事人所聲明之證據範圍的限制。比較辯論主義與職權探知主義的内涵可得知,自認乃為充分尊重當事人兩造之意思表示的辯論主義之民事訴訟所獨有,而職權探知主義以發現案件事實真相為第一要義,對當事人兩造意思表示之尊重則退居其次,故其無自認制度之适用基礎。
綜觀我國現行民訴法,似仍采職權探知主義,具體理由有三:
其一,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并無拘束受訴法院裁判基礎資料範圍之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款“當事人拒絕陳述的,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之規定即為适證。
其二,民訴法第63條規定:“證據有下列幾種:(一)書證;(二)物證;(三)視聽資料;(四)證人證言;(五)當事人陳述;(六)鑒定結論;(七)勘驗筆錄。以上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據此可知,在現行立法上,當事人的陳述乃一獨立之證據資料,[4]也即在現行立法層面,當事人是作為一證據方法而存在的。正是由于現行立法僅将當事人作為證據方法而未明确賦予其訴訟資料提供主體之地位,當事人的陳述并不具有辯論主義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之應有功能,故即便在當事人陳述中,當事人之間不存在争執之事實,受訴法院也應調查其真僞而不能直接采用,同法第71條第1款“人民法院對當事人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确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即明示斯旨。
其三,民訴法第64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由此可知,在我國,受訴法院認定案件事實不受當事人所聲明的證據方法之限制,在當事人聲明的證據以外,為審理案件的需要,受訴法院自可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
正是由于現行立法仍采職權探知主義,故自認制度尚無立足之本。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楊建華先生所言,“自認之事實所以亦無須證明,系基于辯論主義而來,故于不采取辯論主義制度之大陸,即不承認之”。[5]
或許有人認為,即便現行立法未采辯論主義而無自認之适用,司法解釋未嘗不能對立法予以突破,規定自認制度,并将自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一種予以規範。對此,我們認為,即便承認司法解釋能夠突破現行立法,創制某一立法上未規範之制度,僅就技術規範層面着眼,亦斷難認司法解釋可以單獨創設自認制度。這是因為,作為辯論主義核心要義之一的自認,其與辯論主義的其他要義桴鼓相應,殊難割裂單獨予以規範。因此,隻有在全方位承受辯論主義之前提下,自認之規範始有其合理性。
三、自然規律及定理乃受訴法院認定事實之前提。并非免證事實
嚴格講來,“自然規律”及“定理”并非一純粹法學術語,依《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自然規律”乃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客觀事物内部的規律”。“定理”指的是“已經證明具有正确性,可以作為原則或規律的命題或公式”。從内涵上講,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定理,皆乃人們從生活行為經驗中獲得的關于事物間因果關系或性質狀态的知識或法則。[6]從外延上講,自然規律及定理乃經驗法則的一部分,誠如我國台灣地區一位學者雷萬來所言:“經驗法則……就内容而言,包括一切以自然科學的方法檢驗或觀察自然現象歸納之自然法則;支配人類思考作用之倫理法則、數學上之原理、社會生活之道義、倫理及慣例、交易上之習慣;以及有關學術、藝術、技術、商業及工業等一切生活活動之一切法則。”[7]顯而易見,自然規律和定理皆為脫離具體事實之抽象知識法則,二者均系法律三段論推論之大前提,為受訴法院判斷事實時所應遵循之基準。而免證事實就其本質而言,究為某一具體事實,是法律三段論推論的小前提,因此,司法解釋将自然規律和定理定位為免證事實,其之不當至為顯然。
四、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生效仲裁裁決所确認之事實及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之事實乃特殊公文書所載明之事實,并非免證事實
《适用意見》與《證據規定》皆将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予以規範,絕非妥适,這是因為:
其一,從邏輯上予以考察,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實際上是生效裁判文書所載明之事實,也即該事實乃以生效裁判文書為其載體。故該事實就其本質而言仍為證據資料之一種,并以生效裁判文書為其證據方法。而免證事實從本質上講,乃無需通過證據調查即可由受訴法院确認之事實,該事實之認定與受訴法院之證據調查無涉。因此,将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在邏輯上顯然難以立足。
其二,即便認為現行司法解釋将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蘊含直接賦予生效裁判文書具有實質證據力之旨也難以成立,因為此舉不僅與現行立法之精神有違,也與訴訟理論不相契合。依民訴法第65條第2款“人民法院對有關單位和個人提出的證明文書,應當辨别真僞,審查确定其效力”之規定可以得知,在我國,無論是公文書,還是私文書,[8]均不當然具有實質的證據力。是否具有證據效力需要受訴法院在雙方當事人言詞辯論的基礎上斟酌判斷。按諸訴訟理論,公文書與私文書之區别主要表現在形式證據力之認定這一層面。[9]具體來講,如果為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明其為真正;并且若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推定其為真正;若為公文書,法律直接推定其具有形式證據力,法官無自由心證之餘地。[10]至于實質證據力,不論公文書還是私文書皆賴法官依自由心證為具體判斷,公文書絕無當然具有實質證據力之理。無論該公文書為法院之刑事裁判書還是民事裁判書皆然。誠如我國台灣地區一位學者吳光陸所言:“民事法院不可徑以刑事判決為據即認有證明力,仍因就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憑據辯論調查,以決定該判決書有無證明力,至若它案之民事判決亦同,并非當然有證明力。”[11]《證據規定》将生效裁判書所确認之事實确定為免證事實,也即直接賦予生效裁判文書以實質證據力,無異于剝奪了受訴法院對該特殊書證内容之自由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講,該項規定顯有法定證據主義之色彩),妨礙了受案法官對案件事實心證的形成,對當事人未免過酷。
至于在制作程序之保障上遠較裁判書為弱的仲裁裁決書以及公證文書更不應賦予其實質證據力,因此,《證據規定》将生效仲裁裁決所确認的事實及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不妥自不待言。
五、免證事實之适用
一如上述,在現行民訴法之框架下,惟衆所周知之事實與推定的事實方可成為民事訴訟中之免證事實。但由于兩者成為免證事實之基礎不同,在适用上自然存在較大差異。
(一)衆所周知之事實
所謂衆所周知之事實,是指具有一般知識與經驗之不特定的普通人都相信,且會在毫無懷疑的程度上予以相信的事實。法官以此作為裁判基礎時,由于其具有公知的客觀性,無需經由當事人舉證證明,即會在内心達到對該事實确信的狀态。
衆所周知之事實之所以無需由當事人舉證證明,乃由于其本身固有的顯著性與客觀真實性使然,故将衆所周知之事實明定為免證事實,乃各國立法上之通例,無論其采辯論主義還是采職權探知主義皆然。一般而言,某一項事實作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其一,訴訟發生時,該事實為社會上一般成員所知曉。故某一事實若僅為具有特定職業、地位的人所知悉,而非一般人所知曉,即不屬于衆所周知之事實。全國範圍内一般成員所知曉之事實固然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受訴法院轄區内多數人所周知之事實也應被理解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其二,該事實同時也為受訴法院之法官所知曉。在獨任制下,因隻一名法官為審判,該事實需該獨任法官知曉自無疑義;在合議制下,依通說,其隻需合議庭多數法官知悉即可,而不必要求合議庭所有成員均對該事實有所知曉。因為合議庭成員受教育程度及生活經驗不盡相同,若某一事實因少數法官不知而認其為非衆所周知之事實,徒增當事人舉證負擔,亦有違合議庭多數決議的原則。至于第二審法院對于第一審法院認定的衆所周知之事實之審查自亦應以其是否為第一審法院管轄區域内一般社會成員所周知為斷,而不得以第二審法院管轄區域内社會成員是否知悉為标準。
當然,如某事實并非顯著,或當事人之間對其有争執,自然即非衆所周知之事實。在采辯論主義之立法例的國家或地區,對于衆所周知之事實是否也必須經由當事人主張,向有兩說:一為“積極說”;另一為“消極說”.前者認為,某一事實縱為衆所周知之事實,也須經由當事人主張,受訴法院始可采納。也即,受訴法院對于衆所周知事實之認定仍受主張責任之規制。而後者則認為,對于衆所周知之事實,受訴法院可依職權直接予以認定而無待當事人主張。[12]由于我國民事訴訟不采辯論主義,受訴法院自然可依職權直接認定衆所周知之事實。當然,為維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受訴法院認定該衆所周知之事實時,應賦予因該事實被認定而處于不利地位的一方當事人在法庭辯論時闡述不同意見、提出相反證據的機會。《證據規定》第9條第2款亦明示斯旨。
(二)推定之事實
從理論上講,推定分為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所謂法律上的推定,乃是指“法律本于他事實,而認定某事實為真僞之規定”。[13]所謂事實上的推定,乃是指受訴法院依據已明了之事實(已經證明的事實或不要證事實),運用經驗法則,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僞。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在适用上存在本質上的差别,主要表現為:在法律上的推定,由于推定事實乃法律規範預先創設,故基礎事實一旦被予以證明,法官即必須按照該法律上的規範認定推定事實之存在。因此,對于法律上推定事實之認定,法官并無自由斟酌判斷之餘地。就此而言,法律上的推定改變了證明的主題。而事實上的推定乃法官依據經驗法則,基于自由心證所為之邏輯推論。由于該推定事實非法律預先規定之事實,僅為法官依據經驗法則所得心證之結果。故在事實上的推定,證明主題并無改變。正因為二者存在上述之本質區别,使得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影響迥然相異。也即法律上的推定乃實體法規範,直接導緻舉證責任之轉移,因此對造當事人欲反駁推定事實必須提供本證,讓法官對該推定事實之不存在達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始為成功。而事實上的推定并不使舉證責任發生轉移,對于該推定事實自始至終由主張其存在的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故對方當事人為反駁該推定事實,隻須提供反證據,讓法官對該推定事實形成不了内心确信,也即使該事實處于真僞不明狀态即可。
從《證據規定》第9條第2款的規定看,不管是對法律上推定的事實還是對事實上推定的事實之反駁,均要求當事人提出“足以推翻”之證據,根本未注意到反駁這兩種推定事實在證明要求上并非同一,其結果,在受訴法院适用事實上的推定時必然會加重反駁推定事實存在之當事人之舉證負擔,對當事人兩造之公平保護殊欠周全。
六、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1)在尚未确立辯論主義之現階段,民事訴訟應無自認制度之适用,自認之事實當然不能作為免證事實;(2)自然規律及定理從本質上講,乃經驗法則之一部分,是法院認定案件事實之前提,自非免證事實;(3)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生效仲裁裁決所确認之事實及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之事實從性質上講,乃生效裁判書、生效仲裁裁決書及公證文書所載明之事實,前揭文書并無當然之實質證據力,故也不應将其所載明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對待。在現行民事訴訟框架之下,隻有衆所周知之事實及推定之事實始可納入免證事實範疇,惟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對其适用時,應合理界定衆所周知之事實之界域,區分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俾于訴訟理論相侔。
【作者簡介】
占善剛,單位為武漢大學;劉顯鵬,單位為武漢大學。
【注釋】
[1]從訴訟理論上講,自認乃是指在民事訴訟中,一方當事人對對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不利于己之事實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所作的承認。因此,自認的對象僅為對該當事人不利的事實。《證據規定》第8條并未對此予以明确區分,故嚴格講來,其尚未确立真正意義上的自認制度。
[2]自認與對訴訟請求的承認乃兩種不同制度。從訴訟理論上講,兩者差别主要表現為:(1)後果不同。對于自認的事實受訴法院可直接予以裁判确認,從而免除自認當事人對造的舉證責任。而對訴訟請求的承認即意味着對訴訟标的的認諾,受訴法院可直接基于該行為作出該方當事人敗訴的判決。(2)主體不同。自認的主體可以是當事人任何一造,而對訴訟請求的承認之主體隻能是被告。
[3]關于民事訴訟采納辯論主義的根據,參見駱永家:《既判力之研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台灣三民書局1999年版,第207頁。
[4]從理論上講,所謂證據資料,乃是指受訴法院經由證據方法之調查所獲得的用以形成心證的事實。所謂證據方法指的是可由受訴法院予以調查的客觀載體。證據方法之作用在于受訴法院對其予以調查可獲得相應之證據資料。根據載體的不同,證據方法可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方法。與我國将當事人作為人的證據方法不同的是,在采辯論主義的德國、日本及我國台灣地區,當事人乃訴訟資料之主體,并非一獨立之證據方法,受訴法院對當事人的詢問僅為證據調查之輔助手段,也即受訴法院隻有在對其他證據進行調查後仍不能獲得對案件事實之心證始可為之。參見《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45條、《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17條及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367條。雖然近來德、日及我國台灣地區為促進案件審理之集中化,加大了法官詢問當事人之力度,惟依學者之解釋,法官詢問當事人仍應在無法通過其他證據調查獲得心證時始可适用,以免動搖辯論主義之根基。參見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台灣三民書局2002年8月版。第427頁。
[5]楊建華主編:《海峽兩岸民事程序法論》,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7頁。
[6]參見駱永家:《民事舉證責任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7頁。
[7]雷萬來:《民事證據法論》,台灣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頁。
[8]從訴訟理論上講,文書(書證)分為公文書和私文書兩種。所謂公文書,乃指機關或公務員按其職務依照法定方式所制作之文書;與其相對,即為私文書。見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三民書局2002年版,第398頁。現行立法雖然不承認公文書與私文書之分類,但依《證據規定》第77條“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之規定可知,民事審判實踐尚承認二者之分類。
[9]在大陸法系,文書(書證)的證據力分為形式證據力和實質證據力。“文書真正成立時所存在之證據力,亦即足證其做成人實曾為文書内所記載之陳述或報告,是為形式上之證據力;文書所記載事項得據為判斷材料時所存之證據力,亦即文書之内容,是為某事項之證明,是為實質上之證據力。文書的形式證據力是文書實質證據力的前提條件,文書必須首先具有形式證據力才有判斷其實質證據力的必要”。前引[8],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書,第398頁。
[10] 前引[8],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書,第398頁。
[11]吳光陸:“判決是否當然有證據力”,載《月旦法學雜志》第32期,第13頁。
[12]參見前引[6],駱永家書,第35頁。
[13]前引[8],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書,第260頁。
【出處】《法學評論》2004年第4期
【摘要】本文依證據法之基本理論,結合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以獨特的視角對現行司法解釋中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作了全方位的檢視。本文認為,在現行民事訴訟運作模式下,惟衆所周知之事實與推定之事實始屬免證事實。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對這兩項該免證事實之适用分别作了闡析。
【關鍵詞】免證事實;辯論主義;證明力
【寫作年份】2004年
【正文】
在民事訴訟理論上,免證事實又稱不要證事實,乃指無須經由當事人兩造提供證據予以證明,而可直接由受訴法院裁判确認之事實。因現代民事訴訟皆采證據裁判主義,受訴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端以證據為基礎,故免證事實乃為證據裁判主義之例外。又因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兩造負舉證之責,故免證事實同時構成舉證責任之例外。由于免證事實攸關當事人舉證責任之界阈,關乎當事人兩造利益至巨,故各國立法例皆對免證事實予以明确界定,以杜受訴法院恣意濫用之弊。盡管我國現行民訴法并未明定哪些事實無需當事人舉證,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适用意見》)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幹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則先後對免證事實作了相對明确之界定,從而部分為民事審判實踐中受訴法院認定免證事實提供了依據。然則細細推究該兩項司法解釋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不難窺見,其存在諸多與現行立法結構和相關訴訟理論相乖悖之罅漏。舉其荦荦大者,尤以免證事實範圍之不當與适用之失範為著。是故,從理論上厘定現行法框架下免證事實之應有範圍并對其正确适用予以闡說洵屬必要。本文之寫作即是基于此一目的之考量。
一、免證事實在現行司法解釋上的體現
雖然現行民訴法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付之阙如,然《适用意見》第75條和《證據規定》第8條、第9條,則皆對免證事實之範圍作了相對明确之界定。
《适用意見》第75條規定:“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1)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和提出的訴訟請求,明确表示承認的;(2)衆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及定理;(3)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4)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實;(5)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證據規定》第8條第1、2款規定:“(第1款)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确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除外。(第2款)對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未表示承認也未否認,經審判人員充分說明并詢問後,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證據規定》第9條規定:“(第1款)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一)衆所周知的事實;(二)自然規律及定理;(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四)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認的事實;(五)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确認的事實;(六)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第2款)前款(一)、(三)、(四)、(五)、(六)項,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盡管《适用意見》第75條關于免證事實之規範依“新法優于舊法”之法律适用原則,不再具有指導民事審判實踐的效力,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在學理研究上的價值。這是因為,将最高人民法院于不同年代(《适用意見》于1992年公布,《證據規定》于2001年公布)對同一制度所作的規範予以比較考察,不僅能窺見司法解釋制定者關于此項制度适用之價值取向上的更易,從而為将來立法者之價值抉擇提供參考,并且能夠為将來的立法提供部分之實證資料,從而裨益于立法之完善。本此之旨,本文試對該兩項規範比較如下:
其一,《證據規定》第8條第1、2款分别規範了明示的自認與默示的自認,[1]并明定兩者皆為免證事實。與《适用意見》第1項相比,《證據規定》不僅增加了拟制的自認制度,從而将拟制自認之事實亦納入免證事實之範圍,并且注意到了《适用意見》第1項“一方當事人對訴訟請求的承認”在效力上與自認尚非同一,[2]并将其擯除在免證事實之外,足資認同。
其二,《證據規定》第9條一改《适用意見》第75條将“衆所周知的事實”與“自然規律及定理”并列規範之樣式,于第(二)項、第(三)項對二者予以分列誠屬妥适。這是因為“衆所周知的事實”與“自然規律及定理”從内涵上講并非同一層面之事物,将其并列從邏輯上講殊非妥當。
其三,相對于《适用意見》第75條,《證據規定》第9條增列“仲裁裁決所确認的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一。窺其緣由,我們認為可能是因為《适用意見》公布之時,仲裁尚不采一裁終局制,仲裁裁決作出後,當事人不服仍可向法院起訴,故将仲裁裁決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尚存在制度上的障礙。
其四,依《證據規定》第9條第2款可知,受訴法院關于免證事實之适用并非絕對。表現為除“自然規律及定理”外,其他各項免證事實均允許對方當事人提供相反的證據予以推翻。
盡管如此,《證據規定》與《适用意見》在免證事實範圍的界定上,從整體上看幾乎同一,這充分表明法律适用者關于免證事實應有之義的認識并未有實質性的改變,《适用意見》所存在的舛誤仍為《證據規定》所沿襲。我們認為,其根本緣由在于法律适用者對現行民事訴訟之運作模式及相關訴訟理論缺乏基本認識。在我們看來,以現行民事訴訟運作模式為斷,自認之事實并不能稱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衡諸相關訴訟理論,自然規律及定理,生效裁判所确認的事實,仲裁裁決所确認的事實,有效公證文書所确認的事實亦不能當然地作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在現行民訴法之框架下,惟衆所周知的事實與推定的事實始能成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
二、自認的事實不能作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
自認的事實之所以不能作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認乃辯論主義之産物,在采職權探知主義之我國決無适用之餘地。現代各國民事訴訟,就當事人對訴訟資料(證據資料)之提供與受訴法院認定案件事實之關系而言,殆有兩種運作模式:一日辯論主義,二日職權探知主義。辯論主義包括三層要義:其一,受訴法院不能斟酌當事人兩造未主張之事實作為判決之基礎資料;其二,對于當事人兩造之間無争執之事實(自認、拟制自認),受訴法院無需調查證據,可直接采納作為判決的基礎資料;其三,受訴法院對于當事人兩造争執之事實,應依當事人所聲明之證據予以調查。[3]而職權探知主義在内涵上與辯論主義截然相左,表現為:其一,對于當事人兩造未主張之事實,受訴法院亦可将其作為裁判的基礎;其二,對于當事人兩造之間無争執之事實,受訴法院仍需調查其真僞,而不能直接采納作為判決之基礎資料;其三,受訴法院對事實之調查不受當事人所聲明之證據範圍的限制。比較辯論主義與職權探知主義的内涵可得知,自認乃為充分尊重當事人兩造之意思表示的辯論主義之民事訴訟所獨有,而職權探知主義以發現案件事實真相為第一要義,對當事人兩造意思表示之尊重則退居其次,故其無自認制度之适用基礎。
綜觀我國現行民訴法,似仍采職權探知主義,具體理由有三:
其一,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并無拘束受訴法院裁判基礎資料範圍之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款“當事人拒絕陳述的,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之規定即為适證。
其二,民訴法第63條規定:“證據有下列幾種:(一)書證;(二)物證;(三)視聽資料;(四)證人證言;(五)當事人陳述;(六)鑒定結論;(七)勘驗筆錄。以上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據此可知,在現行立法上,當事人的陳述乃一獨立之證據資料,[4]也即在現行立法層面,當事人是作為一證據方法而存在的。正是由于現行立法僅将當事人作為證據方法而未明确賦予其訴訟資料提供主體之地位,當事人的陳述并不具有辯論主義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之應有功能,故即便在當事人陳述中,當事人之間不存在争執之事實,受訴法院也應調查其真僞而不能直接采用,同法第71條第1款“人民法院對當事人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确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即明示斯旨。
其三,民訴法第64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由此可知,在我國,受訴法院認定案件事實不受當事人所聲明的證據方法之限制,在當事人聲明的證據以外,為審理案件的需要,受訴法院自可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
正是由于現行立法仍采職權探知主義,故自認制度尚無立足之本。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楊建華先生所言,“自認之事實所以亦無須證明,系基于辯論主義而來,故于不采取辯論主義制度之大陸,即不承認之”。[5]
或許有人認為,即便現行立法未采辯論主義而無自認之适用,司法解釋未嘗不能對立法予以突破,規定自認制度,并将自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一種予以規範。對此,我們認為,即便承認司法解釋能夠突破現行立法,創制某一立法上未規範之制度,僅就技術規範層面着眼,亦斷難認司法解釋可以單獨創設自認制度。這是因為,作為辯論主義核心要義之一的自認,其與辯論主義的其他要義桴鼓相應,殊難割裂單獨予以規範。因此,隻有在全方位承受辯論主義之前提下,自認之規範始有其合理性。
三、自然規律及定理乃受訴法院認定事實之前提。并非免證事實
嚴格講來,“自然規律”及“定理”并非一純粹法學術語,依《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自然規律”乃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客觀事物内部的規律”。“定理”指的是“已經證明具有正确性,可以作為原則或規律的命題或公式”。從内涵上講,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定理,皆乃人們從生活行為經驗中獲得的關于事物間因果關系或性質狀态的知識或法則。[6]從外延上講,自然規律及定理乃經驗法則的一部分,誠如我國台灣地區一位學者雷萬來所言:“經驗法則……就内容而言,包括一切以自然科學的方法檢驗或觀察自然現象歸納之自然法則;支配人類思考作用之倫理法則、數學上之原理、社會生活之道義、倫理及慣例、交易上之習慣;以及有關學術、藝術、技術、商業及工業等一切生活活動之一切法則。”[7]顯而易見,自然規律和定理皆為脫離具體事實之抽象知識法則,二者均系法律三段論推論之大前提,為受訴法院判斷事實時所應遵循之基準。而免證事實就其本質而言,究為某一具體事實,是法律三段論推論的小前提,因此,司法解釋将自然規律和定理定位為免證事實,其之不當至為顯然。
四、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生效仲裁裁決所确認之事實及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之事實乃特殊公文書所載明之事實,并非免證事實
《适用意見》與《證據規定》皆将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予以規範,絕非妥适,這是因為:
其一,從邏輯上予以考察,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實際上是生效裁判文書所載明之事實,也即該事實乃以生效裁判文書為其載體。故該事實就其本質而言仍為證據資料之一種,并以生效裁判文書為其證據方法。而免證事實從本質上講,乃無需通過證據調查即可由受訴法院确認之事實,該事實之認定與受訴法院之證據調查無涉。因此,将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在邏輯上顯然難以立足。
其二,即便認為現行司法解釋将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蘊含直接賦予生效裁判文書具有實質證據力之旨也難以成立,因為此舉不僅與現行立法之精神有違,也與訴訟理論不相契合。依民訴法第65條第2款“人民法院對有關單位和個人提出的證明文書,應當辨别真僞,審查确定其效力”之規定可以得知,在我國,無論是公文書,還是私文書,[8]均不當然具有實質的證據力。是否具有證據效力需要受訴法院在雙方當事人言詞辯論的基礎上斟酌判斷。按諸訴訟理論,公文書與私文書之區别主要表現在形式證據力之認定這一層面。[9]具體來講,如果為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明其為真正;并且若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推定其為真正;若為公文書,法律直接推定其具有形式證據力,法官無自由心證之餘地。[10]至于實質證據力,不論公文書還是私文書皆賴法官依自由心證為具體判斷,公文書絕無當然具有實質證據力之理。無論該公文書為法院之刑事裁判書還是民事裁判書皆然。誠如我國台灣地區一位學者吳光陸所言:“民事法院不可徑以刑事判決為據即認有證明力,仍因就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憑據辯論調查,以決定該判決書有無證明力,至若它案之民事判決亦同,并非當然有證明力。”[11]《證據規定》将生效裁判書所确認之事實确定為免證事實,也即直接賦予生效裁判文書以實質證據力,無異于剝奪了受訴法院對該特殊書證内容之自由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講,該項規定顯有法定證據主義之色彩),妨礙了受案法官對案件事實心證的形成,對當事人未免過酷。
至于在制作程序之保障上遠較裁判書為弱的仲裁裁決書以及公證文書更不應賦予其實質證據力,因此,《證據規定》将生效仲裁裁決所确認的事實及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不妥自不待言。
五、免證事實之适用
一如上述,在現行民訴法之框架下,惟衆所周知之事實與推定的事實方可成為民事訴訟中之免證事實。但由于兩者成為免證事實之基礎不同,在适用上自然存在較大差異。
(一)衆所周知之事實
所謂衆所周知之事實,是指具有一般知識與經驗之不特定的普通人都相信,且會在毫無懷疑的程度上予以相信的事實。法官以此作為裁判基礎時,由于其具有公知的客觀性,無需經由當事人舉證證明,即會在内心達到對該事實确信的狀态。
衆所周知之事實之所以無需由當事人舉證證明,乃由于其本身固有的顯著性與客觀真實性使然,故将衆所周知之事實明定為免證事實,乃各國立法上之通例,無論其采辯論主義還是采職權探知主義皆然。一般而言,某一項事實作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其一,訴訟發生時,該事實為社會上一般成員所知曉。故某一事實若僅為具有特定職業、地位的人所知悉,而非一般人所知曉,即不屬于衆所周知之事實。全國範圍内一般成員所知曉之事實固然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受訴法院轄區内多數人所周知之事實也應被理解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其二,該事實同時也為受訴法院之法官所知曉。在獨任制下,因隻一名法官為審判,該事實需該獨任法官知曉自無疑義;在合議制下,依通說,其隻需合議庭多數法官知悉即可,而不必要求合議庭所有成員均對該事實有所知曉。因為合議庭成員受教育程度及生活經驗不盡相同,若某一事實因少數法官不知而認其為非衆所周知之事實,徒增當事人舉證負擔,亦有違合議庭多數決議的原則。至于第二審法院對于第一審法院認定的衆所周知之事實之審查自亦應以其是否為第一審法院管轄區域内一般社會成員所周知為斷,而不得以第二審法院管轄區域内社會成員是否知悉為标準。
當然,如某事實并非顯著,或當事人之間對其有争執,自然即非衆所周知之事實。在采辯論主義之立法例的國家或地區,對于衆所周知之事實是否也必須經由當事人主張,向有兩說:一為“積極說”;另一為“消極說”.前者認為,某一事實縱為衆所周知之事實,也須經由當事人主張,受訴法院始可采納。也即,受訴法院對于衆所周知事實之認定仍受主張責任之規制。而後者則認為,對于衆所周知之事實,受訴法院可依職權直接予以認定而無待當事人主張。[12]由于我國民事訴訟不采辯論主義,受訴法院自然可依職權直接認定衆所周知之事實。當然,為維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受訴法院認定該衆所周知之事實時,應賦予因該事實被認定而處于不利地位的一方當事人在法庭辯論時闡述不同意見、提出相反證據的機會。《證據規定》第9條第2款亦明示斯旨。
(二)推定之事實
從理論上講,推定分為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所謂法律上的推定,乃是指“法律本于他事實,而認定某事實為真僞之規定”。[13]所謂事實上的推定,乃是指受訴法院依據已明了之事實(已經證明的事實或不要證事實),運用經驗法則,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僞。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在适用上存在本質上的差别,主要表現為:在法律上的推定,由于推定事實乃法律規範預先創設,故基礎事實一旦被予以證明,法官即必須按照該法律上的規範認定推定事實之存在。因此,對于法律上推定事實之認定,法官并無自由斟酌判斷之餘地。就此而言,法律上的推定改變了證明的主題。而事實上的推定乃法官依據經驗法則,基于自由心證所為之邏輯推論。由于該推定事實非法律預先規定之事實,僅為法官依據經驗法則所得心證之結果。故在事實上的推定,證明主題并無改變。正因為二者存在上述之本質區别,使得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影響迥然相異。也即法律上的推定乃實體法規範,直接導緻舉證責任之轉移,因此對造當事人欲反駁推定事實必須提供本證,讓法官對該推定事實之不存在達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始為成功。而事實上的推定并不使舉證責任發生轉移,對于該推定事實自始至終由主張其存在的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故對方當事人為反駁該推定事實,隻須提供反證據,讓法官對該推定事實形成不了内心确信,也即使該事實處于真僞不明狀态即可。
從《證據規定》第9條第2款的規定看,不管是對法律上推定的事實還是對事實上推定的事實之反駁,均要求當事人提出“足以推翻”之證據,根本未注意到反駁這兩種推定事實在證明要求上并非同一,其結果,在受訴法院适用事實上的推定時必然會加重反駁推定事實存在之當事人之舉證負擔,對當事人兩造之公平保護殊欠周全。
六、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1)在尚未确立辯論主義之現階段,民事訴訟應無自認制度之适用,自認之事實當然不能作為免證事實;(2)自然規律及定理從本質上講,乃經驗法則之一部分,是法院認定案件事實之前提,自非免證事實;(3)生效裁判所确認之事實、生效仲裁裁決所确認之事實及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之事實從性質上講,乃生效裁判書、生效仲裁裁決書及公證文書所載明之事實,前揭文書并無當然之實質證據力,故也不應将其所載明之事實作為免證事實之對待。在現行民事訴訟框架之下,隻有衆所周知之事實及推定之事實始可納入免證事實範疇,惟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對其适用時,應合理界定衆所周知之事實之界域,區分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俾于訴訟理論相侔。
【作者簡介】
占善剛,單位為武漢大學;劉顯鵬,單位為武漢大學。
【注釋】
[1]從訴訟理論上講,自認乃是指在民事訴訟中,一方當事人對對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不利于己之事實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所作的承認。因此,自認的對象僅為對該當事人不利的事實。《證據規定》第8條并未對此予以明确區分,故嚴格講來,其尚未确立真正意義上的自認制度。
[2]自認與對訴訟請求的承認乃兩種不同制度。從訴訟理論上講,兩者差别主要表現為:(1)後果不同。對于自認的事實受訴法院可直接予以裁判确認,從而免除自認當事人對造的舉證責任。而對訴訟請求的承認即意味着對訴訟标的的認諾,受訴法院可直接基于該行為作出該方當事人敗訴的判決。(2)主體不同。自認的主體可以是當事人任何一造,而對訴訟請求的承認之主體隻能是被告。
[3]關于民事訴訟采納辯論主義的根據,參見駱永家:《既判力之研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台灣三民書局1999年版,第207頁。
[4]從理論上講,所謂證據資料,乃是指受訴法院經由證據方法之調查所獲得的用以形成心證的事實。所謂證據方法指的是可由受訴法院予以調查的客觀載體。證據方法之作用在于受訴法院對其予以調查可獲得相應之證據資料。根據載體的不同,證據方法可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方法。與我國将當事人作為人的證據方法不同的是,在采辯論主義的德國、日本及我國台灣地區,當事人乃訴訟資料之主體,并非一獨立之證據方法,受訴法院對當事人的詢問僅為證據調查之輔助手段,也即受訴法院隻有在對其他證據進行調查後仍不能獲得對案件事實之心證始可為之。參見《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45條、《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17條及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367條。雖然近來德、日及我國台灣地區為促進案件審理之集中化,加大了法官詢問當事人之力度,惟依學者之解釋,法官詢問當事人仍應在無法通過其他證據調查獲得心證時始可适用,以免動搖辯論主義之根基。參見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台灣三民書局2002年8月版。第427頁。
[5]楊建華主編:《海峽兩岸民事程序法論》,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7頁。
[6]參見駱永家:《民事舉證責任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7頁。
[7]雷萬來:《民事證據法論》,台灣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頁。
[8]從訴訟理論上講,文書(書證)分為公文書和私文書兩種。所謂公文書,乃指機關或公務員按其職務依照法定方式所制作之文書;與其相對,即為私文書。見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三民書局2002年版,第398頁。現行立法雖然不承認公文書與私文書之分類,但依《證據規定》第77條“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之規定可知,民事審判實踐尚承認二者之分類。
[9]在大陸法系,文書(書證)的證據力分為形式證據力和實質證據力。“文書真正成立時所存在之證據力,亦即足證其做成人實曾為文書内所記載之陳述或報告,是為形式上之證據力;文書所記載事項得據為判斷材料時所存之證據力,亦即文書之内容,是為某事項之證明,是為實質上之證據力。文書的形式證據力是文書實質證據力的前提條件,文書必須首先具有形式證據力才有判斷其實質證據力的必要”。前引[8],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書,第398頁。
[10] 前引[8],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書,第398頁。
[11]吳光陸:“判決是否當然有證據力”,載《月旦法學雜志》第32期,第13頁。
[12]參見前引[6],駱永家書,第35頁。
[13]前引[8],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書,第260頁。
你可能想看: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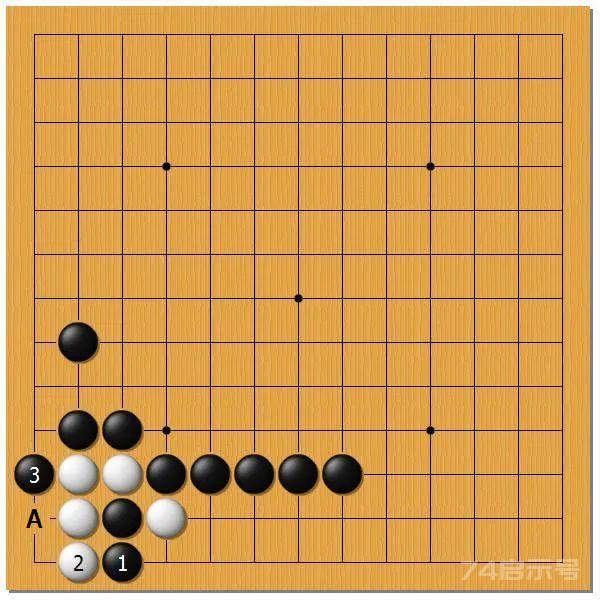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