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
- 文化
- 6天前
- 221

安徒生
“《卖火柴的女儿》是我有一次出国旅行,路上在格拉司丁堡停留了几天的时候写的”,回忆起那次兴之所至的创作经历,安徒生说道,“当时我接到福林克君一封信,要我照着他信内附来的三张画片之一,替他的历书里作一篇故事。我所挑的一张是一个女孩子拿着许多火柴的画片” (安徒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他绝不会料想到,这篇在行色匆遽中灵光乍现、挥笔立就,与一般童话判然有别的小故事,时隔约半个世纪之后,居然会在遥远的中国大受推崇,相继出现过数十种译本,并被选入各类教材和读本,由此还衍生出不少形式各异的文艺作品,吸引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探寻其魅力之所在;而与此同时,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社会环境迁变、意识形态递嬗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其创作主旨又无端招致诸多或有意或无意的漠视、误读乃至斥责、批判。
一、首译的问世与风行
早年以文言翻译过《皇帝之新衣》 (收入《域外小说集》,群益书社,1921年)的周作人,曾经慨叹这类作品“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 (《域外小说集序》)。不过他还是抽出时间改用白话翻译了一篇《卖火柴的女儿》 (载《新青年》第6卷第12号,1919年),并在当年风靡一时。西谛(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 (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中对此给予过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先前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安徒生的作品并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充分重视,“到了‘五四’之后,我们的思想,经了大变化,《新青年》成了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周先生译登在《新青年》上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才为大家所十分注意”,随后以此为契机,“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的有人译了”。从中不难窥知周译《卖火柴的女儿》在安徒生童话汉译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

周作人译《卖火柴的女儿》
周作人此前在《人的文学》 (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中就已经大力倡导创作时应该“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尤其指出,“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而在此过程中绝不能妄自尊大,“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稍后在《平民文学》 (载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署名“仲密”)里,他再次强调文学“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为此他也希望有志者“能翻译或造作出几种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作品”。着手翻译这篇《卖火柴的女儿》,毋庸赘言正是在身体力行自己的这些主张。当看到小女孩在“寒冷阴暗”的雪夜中“光着头,赤着脚”,“冻饿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但在幻觉中又一直憧憬歆羡着“温暖的炉火,好的烧鹅,美丽的圣诞树”,祈求生前疼爱自己的“清净光明,和善可爱”的祖母能够带着自己一同离开,而最终“坐在拐角,靠着墙,两颊绯红,口边带着笑容——在旧年末夜冻死了”,相信每一位善良的普通读者都会为之黯然神伤,一掬同情之泪。周作人在译文最后另附识语,除了根据安徒生的个人自述介绍这篇作品的创作原委,还惋惜当年他运思落笔时所依凭的画片没能留存下来,“但他集内丹麦人Pedersen的插画,有两张小图插在这故事里,也非常得神”;又特别留意到“他写这女儿的幻觉,正与俄国平民诗人Nekrassov的《赤鼻霜》诗里,写农妇在林中冻死时所见过去的情景相似。可以同称近世文学中描写冻死的名篇”。足见他选择这篇童话故事来翻译,事先经过一番细致的蒐求和考量,绝非率尔操觚之举。
周译本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有一段很容易被今人忽略,在现代汉语史上却相当耐人寻味的小波折。汉语中用作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原本只有“他”“其”“伊”“彼”等,并不能据此直接区分男女性别的差异。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周作人为此曾与友人刘半农往还商讨,在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改革》 (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时,他在译者题记中就议及此事,“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然而这个凭空生造的“她”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经过再三斟酌,周作人决定仿效日语中“彼女”的造词法,“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最初发表译作《卖火柴的女儿》时,他也沿用了这一方法,故事中凡是用来指称小女孩的地方,一概使用“他”字后附加小字“女”的方式以示区别。对周作人这样别出机杼的大胆创新,很快有人提出反对和质疑。胡适在翻译莫泊桑的小说《弑父之儿》 (连载于1919年1月26日、2月2日《每周评论》,署名“适”)时,于文末附注内明确提出,“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钱玄同更是直言不讳地批驳这一权宜之计“有些‘不词’”,“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周作人在回应时也坦承,“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用代名词的本意了” (钱、周两人所言俱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卷入了这场论争,有人觉得男女不妨统用“他”字,另有人主张推广使用“她”字,还有人建议改以“伊”字来指称女性。在最初的两三年间,“又基本以主张‘伊’字的人略占上风”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四章《“她”字存废的论争与“她”、“伊”二字的竞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周译《卖火柴的女儿》刊登之后不久便受到许多关注,先后被《时事新报》 (1919年3月21日)和《广益杂志》 (第30期,1922年)转载过,只是前者将原译文中的“他女”统一修改成“他”,后者又将其全部替换为“伊”。另有一篇译者署名为“悟生”的《卖火柴的女儿》 (载1922年11月22日《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41期),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完全将周译本攘为己有,但全篇又都以“她”来指称小女孩,倒是颇有些先见之明。至于周作人自己,对这篇译作无疑也非常满意,相继将其收入《点滴》 (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和《空大鼓》(开明书店,1928年)这两部个人译文集,却又不动声色地将原先使用的“他女”字都改成了“伊”字。这两本书也收入了斯特林堡的那篇《改革》,周作人对译文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并径直删去了开篇那段讨论女性代词用法的题记,显然已经毅然舍弃了原先的主张。

1923年颁布实施了由叶圣陶负责起草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 (收入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附录的《略读书目举例》另由胡适拟定,其中就列有周作人辑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书中收录的这篇《卖火柴的女儿》,因为小主人公与学生年龄相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此后各类教材编纂者青睐的对象。就在这一年6月,由顾颉刚、范祥善、叶圣陶编辑,胡适、王云五、朱经农校订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 (商务印书馆,1923年)率先选录了这篇童话。此后约二十年间,陆续又有朱剑芒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初中国文》 (世界书局,1929年)、赵景深编《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 (北新书局,1930年)、周予同等编《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 (商务印书馆,1932年)、姜亮夫等编《初级中学北新文选》 (北新书局,1932年)、石泉编《初中师范教科书初中国文》 (文化学社,1932年)、罗根泽等编《初中国文选本》 (立达书局,1933年)、贾英编《少年文选》 (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胡杰编《作文法讲话》 (艺文书店,1943年)等二三十种教材和读本,不约而同都将其作为范文。早年从学于周作人的陈介白在选录该篇之余,更是特意邀请周氏为其所编《初中国文教本》(贝满女子中学校,1936年)题写书名以作招徕。
为了指导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这篇童话,这些教材和读本的编选者们也会做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傅东华和陈望道在合作编选《基本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国文》 (商务印书馆,1932年)时,批评普通教本中“有些地方文字浅易却于了解上不得不有一番详细解说的,每多缺漏无注”,认为“倘不详为解说,学生便不能获得具体的观念” (见该书《编辑大意》)。童话中提到小女孩幻想着“坐在一株美丽的圣诞树节树下”,两位编者就很周到地添加了一条详细的注释:“基督教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叫做‘圣诞节’(Christmas Day),前一夜叫做‘圣诞前夜’(Christmas Eve),当夜叫做‘圣诞夜’(Christmas Night)。当圣诞节,凡在信基督教的地方,家家户户都设一株长青树,上面挂着赐给儿童的恩物,以及小灯笼,备圣诞前夜及圣诞夜点蜡烛,这就叫做‘圣诞节树’(Christmas tree)。”有些编选者根据教学的需求,还会对周氏译文做一些调整或加工,尽管实际效果或许未必理想。伪教育总署编审会所编《高小国语教科书》(新民印书馆,1941年)“专供小学高级国语科两学年教学之用”,考虑到学生程度尚浅且教学课时有限,在选录篇章时“有节选的,也有增删的” (见该书《编纂大意》)。兴许是想更贴近中国儿童的日常生活,课文中居然荒唐地把小女孩在街头闻到的“烧鹅的香味”改成了“烧肉的香味”。随后又擅作主张,将小女孩四次划亮火柴后所目睹的各种幻景悉数刊落,只保留了次日清晨她在街头冻毙的结局。这样买椟还珠式的大肆删改显然不足为训,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避免了原作里小女孩幻想中的“烧鹅”与课本编纂者篡改后的“烧肉”之间发生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吧。
二、从转译到直译
周作人的译本虽然大受欢迎,倒也并非一枝独秀。紧随其后就有钵庵翻译的“泰西短篇”《卖火柴之小女》 (载《微言》第5期,1921年;又连载于1924年9月28日、29日《黎明报》)。译者在篇末跋语中说,“原著人之名氏待考,其笔态回旋,文心曲折,助余良非浅鲜”。看来其翻译初衷与林纾所说的外国小说“大类吾古文家言”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载林纾、魏易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卷首,商务印书馆,1905年)并无二致,主要是为了炫耀自家结撰文章的技巧,对安徒生其人其作则不甚了了,也根本无意再续做查考。由于转以文言传述,为使文辞雅驯而颇费心力,可惜有时过犹不及,反倒失之陈腐。开篇叙及“时方隆冬雪后,天气严寒,街市已衔暮景,兼为岁除之夕。有一小女,踯躅道旁,科头赤足,形状至堪怜悯”,所用的“衔暮景”语本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中“复有楼台衔暮景”之句,而“科头赤足”又源出《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略》里的“科头徒跣”。说到小女孩“再擦一根燃之,彼身竟坐于万年枝下”,译者还不得不随文添加注解,交代这里是指“耶稣圣诞木,借译曰万年枝”。这样的译文对一般读者尤其是儿童而言,无疑就显得迂曲生涩,与周氏译文所要竭力呈现的平易如话的风格迥然不同。周作人曾批评使用文言来翻译安徒生童话,无异于“把小儿的言语,变了大家的古文,Andersen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 (《随感录(二四)》,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将这段评语移用过来,恐怕也不算是吹毛求疵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持续推进,此后不断涌现出大批白话译本。为了消除普通读者的疏离感,译者们往往会对个别细节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比如周作人的译文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小女孩整日奔波却没有人给过她“一个钱”,到了天水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儿》 (载1933年10月5日《校风》第82期)里就成了“她不能有一个铜子儿”,黎宗原译《一个卖火柴的少女》 (载《苍中校刊》1934年第2期)则说她“身上还是没有一个铜元”,赵家舜译《卖火柴的女孩》 (载《广东儿童》第5卷第2期,1943年)又称“也没有人给她一个铜板”。经过这样的转换,就比较容易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即便照着西文直译,有些译者也会推己及人地替读者着想。陆士豪译《卖火柴的女孩》 (载《新民》第1卷第5期,1931年)在此处作“她还没有卖去一个辨士的火柴”,当即随文指出,“辨士”是“英国铜币,值十二分之一先令”。熊大桐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2期,1947年)在这里作“也没有人给她一个辨士”,也进一步解释道,“辨士Pence为英国之币名,相当于我国的‘分’”。借助这些提示,即使是初次接触西方作品的读者,大概也不至于产生太多的隔阂感。

陆士豪译《卖火柴的女孩》
不过通观早期的各种白话译本,整体质量依然良莠不齐,并不尽如人意。有些译本存在明显的错谬疏漏,缺乏精益求精的推敲琢磨。例如周作人的译文在开篇时说小女孩“光着头”,本来就已经容易滋生歧义,而到了陆士豪的译本中,居然称小女孩是“秃头的”,可是后文明明又提到“雪花飞到她卷在颈项边的麻色头发上”,浑然不觉叙述时的上下抵牾。张家凤译《卖火柴的小女儿》 (收入《安徒生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40年)讲到小男孩拿走小女孩丢失的一只鞋子,“他说这可以当作玩偶的摇篮用的”,根本没有认真推想,四处游荡的穷苦儿童哪会有什么玩偶?靖宇译《卖火柴的小女孩》 (连载于1934年12月8日、15日《津中周刊》第112、113号)则莫名其妙地把这个小男孩变成了“一群小孩子”,还嚷嚷着“当他们将来自己有了小孩时,足够做摇篮用的啊”,不知道到时候这一只鞋子究竟该如何分配?蒋世焘译《卖火柴的小女孩》 (载《磐石杂志》第1卷第1期,1932年)提到逝去的老祖母在小女孩的幻觉中突然现身,“清楚而光润,好像一个鬼”;与之相似的还有佩纶译《卖火柴的女孩》 (载《章江潮》第2卷第1期,1937年),说老祖母出现时“光耀像个妖精”,都没有根据特殊的语境选择贴切的词汇,显得格外突兀诡异,令人啼笑皆非。非龙译《卖火柴的女孩》 (载1942年6月15日《公教白话报》),更是无中生有地说小女孩弄丢了鞋子后饥寒难耐,“迫得她憻慄不稳,不得不倒在地上爬行”,以致进退失据,与下文所说“她不再往前走了”,“两只已经失了感觉的小腿一蹲”,“靠着屋墙坐在雪泥的地上了”云云自相矛盾。
有些译本则随意删减原作内容,不经意间抹杀了作者在其中蕴含的巧思和深意。如龙一铭译《卖火柴的女孩》 (载《小主人》第4卷第22、23期合刊,1940年)只说小女孩过马路时“鞋都失掉了,一只也找不到”,省略了路过的小男孩顺手牵羊拿走其中一只鞋子的小插曲。大概是嫌其旁逸斜出而无关宏旨,可惜原著活泼生动的意趣却由此减损了许多。《儿童世界》编者所译《卖火柴的女孩》 (载《儿童世界》第23卷第1期,1929年),在结尾处提到“她僵硬冰冷地坐着,怀中藏着几束火柴,其中一束已经烧过了”便戛然而止,全然不顾作者最后还郑重其事提到,旁观者并不知晓小女孩昨晚见过各种美景,而且已经跟随祖母升入天堂去享受新年的欢乐。范泉译《卖火柴的女儿》 (收入《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9年)在讲到小女孩向幻觉中的圣诞树“快乐得伸出了两只手”时,直接把原作里圣诞树上的烛光化作星星,其中一颗从天上划落,于是女孩感慨又有人将要死去等大段内容全部删去。他在编译安徒生童话时说,“为了要切合国内的小读者,曾将原著略加增删”,其中就包括“《卖火柴的女儿》等篇里的鬼神的部分”。他还相当自信地宣称,“这在小读者看来,一定是更会容易接受,而且是不致产生不良的效果吧” (见该书《附记》)。这或许正道出了很多译者在删改原作时的心声,然而如此越俎代庖,恐怕反而损害、曲解了安徒生的本意,无形中会对读者产生不少误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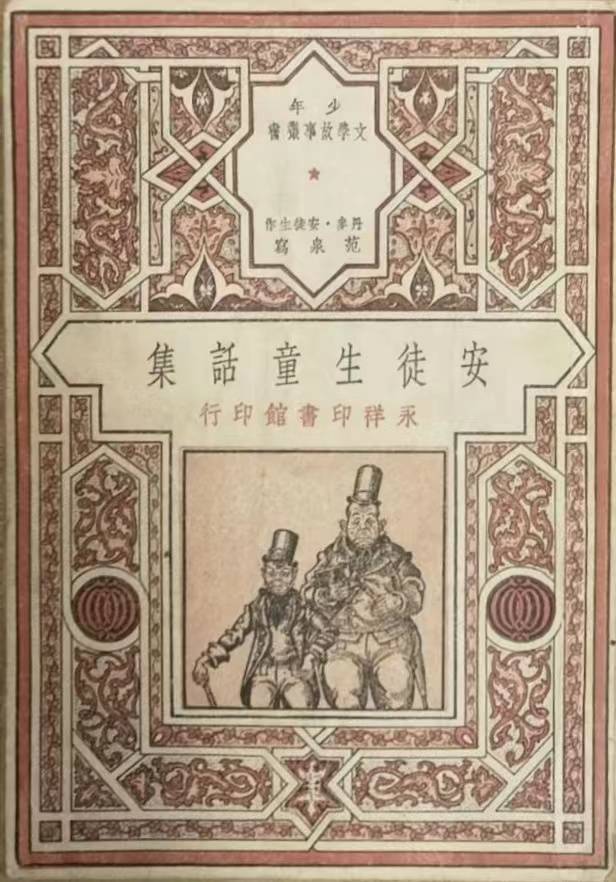
范泉译《安徒生童话集》
稍事比较早期的不同译本,还会发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而又忍俊不禁的问题。以小女孩第二次划亮火柴时眼前所闪现的幻象为例,各位译者就莫衷一是,周作人的译文作“烧鹅肚里满装着苹果干枣”,郭敏学译《卖火柴的小女孩》 (载《橄榄月刊》第12、13期合刊,1931年)作“一只烧鹅,用苹果和梅子喂养的”,蒋世焘译《卖火柴的小女孩》作“一个薰鹅,填着苹果和酸梅”,天水译《卖火柴的小女儿》作“一只熏鹅,李子和苹果做馅心,填在肚皮里”,非龙译《卖火柴的女孩》作“有一盘一盘的热烤鸭,一碟碟的鲜红苹果,和许多乌黑的梅子”,友译《小的卖火柴的女孩》 (载《朝阳》1949年第5期)作“一个热气腾腾的烤鹅,鹅肚内塞满了苹果,和干的梅子、葡萄干等”。小女孩看到的究竟是烧鹅、薰鹅还是烤鸭,名目纷繁的水果和干果到底是馅料、饲料还是另行装盘的食物,着实让眼花缭乱的读者有些无所适从。
各家译文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弊病,除了受到译者个人学识、素养、态度等影响(有些译者应该还只是在读的中学生),与他们当时都未能直接依据丹麦语原本而只能凭借英语、日语等各类转译本也大有关系。甚至直到五十年代后,有些课本在替换译文时,也只是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几种英译本翻译” (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语文》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61年)。经过数度辗转,自然难以准确呈现作品的原貌。鲁迅在《论重译》 (收入《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中早就讨论过重译——即根据其他语种译本进行转译——的话题,感叹“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甚至“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也无从看见了”,所以对此并不求全责备。不过他对通晓丹麦语等小语种的译者仍然满怀期待,认为“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晚清民国之际安徒生的部分作品开始被逐渐译为汉语,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总算盼来精通丹麦语的译者。四十年代长期旅居欧洲的叶君健在自学丹麦语之余开始重温安徒生童话,他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于是跃跃欲试,“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收入周靖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他参酌两种英文版和一种丹麦语版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选集:母亲的故事》 (平明出版社,1954年),其中就收有新译的《卖火柴的女孩》。没过几年,他又完全依照最新版的丹麦语《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修订该书译文,将其作为“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改版付梓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这篇童话的题名也正式改定为《卖火柴的小女孩》。从此叶君健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安徒生作品的译介中,其译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印行流播。此后虽然还有林桦译《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任溶溶译《安徒生童话全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石琴娥译《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译林出版社,2005年)等各具特色的译本不断问世,但论影响之深广,恐怕都难以望其项背。

叶君健

叶君健译《母亲的故事》(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中收录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每逢重印或改版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润饰改订,反复推敲,不厌其烦,即使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内容相对简单的作品也不例外。比如故事开篇,他最初译作“天气冷得可怕。天在下雪,而且快要黑了。晚间——这年的最后的一个晚间——已经到来” (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用语略显累赘拖沓,此后便改易为“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黑暗的夜幕开始垂下来了。这是这年的最后一夜——新年的前夕”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讲到小女孩想要找个地方休息片刻,他起初译作“她在两幢房子——有一幢更伸向街中心一点——所形成的一个墙角里面坐下来” (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语意稍嫌含混不清,就先后修改成“她在两座房子——有一座向着街心比另一座更伸出一点——所形成的一个墙角里坐下来”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她在两座房子——一座比另一座更向街心凸出一点——所构成的一个墙角里坐下来” (收入《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还是不够满意,又改为“那儿有两座房子,其中一座房子比另一座更向街心伸出一点,她便在这个墙角里坐下来” (收入《母亲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前几次的译文大概是为了亦步亦趋地追随原文的表述方式,不免有些诘屈生硬,改定以后顺应了汉语自身的表达特点,就显得文从字顺多了。再如说起小女孩想要形容一下眼前出现的圣诞树,他起初译作“它比上次圣诞节时她透过玻璃门所看到一个富有商人家里的那株还要大,还要美” (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维持了三十年之久,最终还是修改为“上次圣诞节时,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一个富有商人家里的一株圣诞树;可是现在这一株比那一株还要大,还要美”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想必是为了更贴近儿童的语言习惯,才特意把一气呵成的长句拆分成几个简洁明快的短句。透过这些细枝末节,足见他对待译事满怀敬畏之心,没有丝毫轻慢懈怠。

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母亲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旅欧期间叶君健多次前往丹麦小住,对北欧的风俗民情多有亲身体验,在翻译时也藉此给一些情节添加言简意赅的注解。当小女孩闻到“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他在译注中就补充说,“烤鹅肉是丹麦圣诞节和除夕晚餐中的一个主菜”;小女孩看到流星划过天际,感伤道“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译注里又提醒道,“北欧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天上便有一颗星。一颗星的陨落象征一个人的死亡” (据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其后各版又略有修改)。尽管这些解说点到即止而未遑展开,却揭示了文中看似平常无奇的琐屑实则也暗含玄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赘言闲笔,对读者深入体会作者的匠心独运、领略作品的丰富意蕴都颇有裨益。
从周作人到叶君健的几代译者,在翻译这篇童话时历经了从转译到直译的演变。就故事情节的传达而言,毫无疑问是后出转精,越来越臻于准确流畅。不过仔细比勘玩索之后,恐怕仍有些许未能尽惬人意的地方,最显著的一处就是关于这个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周作人的译文在开篇时说这是“一年最末的一晚”,随后又提到“今日正是大年夜了”。此后陈陈相因,几乎所有的译者都采纳了类似的译法。就连叶君健也萧规曹随,忽而说“这是这年最后的一夜——新年的前夕”,忽而又说“这是除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后续林桦、任溶溶、石琴娥等各家译本,也都无一例外。大家都没有留意到,由于中西古今的历法存在根本差异,中国人所熟悉的“大年夜”或“除夕”实际上和西方人所理解的“这年最后的一夜”完全不同。近代以来西潮东渐,在国人对西方历法还较为陌生的情况下,为了消除阅读时的隔膜而采取归化式的译法固然情有可原,但却忽略了如此一来,很容易让读者形成先入为主的误会,以致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非译《卖火柴的小女孩》 (连载于1943年9月8日、9日、10日《崇明新报》)在开篇说这是“旧历年尾的最后一个晚上”,接着又说“这正是除夕之晚”;陈敬容在翻译《卖火柴的女孩》 (收入《沼泽王的女儿》,骆驼书店,1948年)时,也自始至终只说这一天是“大除夕”。然而这样处理同样忽略了中西节日习俗的差异,依旧不能弥缝叙事环节中的阙漏脱节,导致无法与下文所述小女孩幻想着坐在圣诞树下等情节相互衔接呼应。只有极少数译者提到“这是圣西尔维斯特的晚上” (蒋世焘译文。按:“圣西尔维斯特”即古罗马主教Saint Sylvester的音译,其瞻礼日为12月31日),或“是日是圣诞节” (佩纶译文。按:欧洲的圣诞节节期即Christmastide从圣诞节前夜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新年元旦),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不少人眼中,童话翻译只是不足挂齿的薄技微能,然而想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真是谈何容易。
三、从译作到创作
因为长期以来被大量教材、读本选作范文,使这篇童话成为数代人接受情感教育、文学熏陶乃至思想启蒙的必读之作。孩提时代烙下的深刻印象,经由时间的积淀和世事的磨砺,得以不断地滋长蔓衍。小女孩紧紧攥住的火柴虽然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亮,却在日后点燃了许多人的诗思文心,最终衍生出各种取资于此而形式各异的文艺创作。
何其芳追忆过少年时代离开私塾,转而在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经历。令他毕生难忘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英文老师,“介绍一本英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作我们的课外读物”,尽管他并没能通读全书,“但是,其中的《小女人鱼》、《丑小鸭》和《卖火柴的女儿》却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提到的尽管是英译本安徒生童话,但想来他对汉译本也绝不会陌生。这些迷人的童话为他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它们引导我更走进了文学。虽然那不是用分行的形式写的,它们却是真正的诗” (《写诗的经过》,收入《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令他声名鹊起的第一部散文集《画梦录》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又何尝不是借用散文的形式来传达低徊怅惘的诗意呢?恰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觉得那种不分行的抒写更适宜表达我的郁结与颓丧” (《梦中道路》,收入《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画梦录》里有一篇《魔术草》,谈到自己从幼年起就沉浸在“幻想的天地”之中,“许久来我悲哀得很神秘,仿佛徘徊在自己的门外,像失掉了乐园的人,有时真愿去当一个卖火柴的孩子,在寒夜里,在墙外,划一小朵金色的火花像打开一扇窗子,也许可以窥见幸福的眩耀吧”。小女孩在绝望无助时依旧无比虔诚地祈盼着奇迹的发生,这一幕势必深深打动过从小就深陷孤独寂寞的何其芳,因而才信手拈来,将童话中最奇妙的那一瞬间剪裁进自己的作品。

何其芳《魔术草》(收入《画梦录》)
到了晚年何其芳仍然壮心不已,筹划创作一部波澜壮阔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为此还拟定过详细的写作提纲。只可惜数十年来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早就令昔日灵动的想象力和丰沛的创造力消磨殆尽,从他留存下来的部分未完稿 (收入《何其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来看,许多内容几乎沦为政治理念的程式化演绎。不过以他本人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董千里,还是值得稍稍留意的。小说里提到他在读中学时买来英译本《安徒生童话集》,尽管只读了其中的三篇,“然而他就沉浸到那些故事里了。《卖火柴的女儿》,那个贫穷的赤脚的小女孩,在下着雪的冷得可怕的新年前夕,在富有人家的欢度除夕的墙外,在种种幻想中冻僵而死,她是多么令人同情呵!董千里读着读着,好像她就是他的一个曾经有过的小妹妹,或者她就是他自己”。年少时那份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直到暮年时回想起来还是恍在眼前,令人依旧激动不已,总算为这部冗长乏味的封笔之作添上了几分真挚感人的亮色。
“七月诗派”的代表之一曾卓最初对写作萌生兴趣,也和安徒生童话颇有渊源。他在小学时遇到过一位语文老师,向他们推荐了不少课外读物,“如鲁迅的《故乡》、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等,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看到了美丽的文艺园地,而且扩大了对生活的认识。那些抒情性很强的作品感染着我,使我初初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载《诗探索》2001年第1-2辑)。在读完安徒生的这篇童话后,“我们为那个在落着大雪的除夕,蜷缩在高楼的墙角,用火柴的微光温暖自己、照亮自己的梦、终于冻死的小女孩流了泪,从这里认识了人生的一角” (《第一课与第一步》,收入《让火燃着》,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受到这篇童话的启发,他后来写过一首《除夕》 (收入《门》,诗文学社,1944年),为家国沦亡发出过苦痛屈辱的呼喊。诗中悲愤地拷问道:“披着黑色的愁苦的外衣/受难的国度与受难的人民/属于他们自己底狂欢夜/安排在时间无穷线上的哪一端呢?”随即激切地回应说:“不是今日,该也不是昨日的:/那时候还有在大雪中/穿着单薄的破衣/紫色的赤脚徘徊在街头积雪中的/卖火柴的女儿,在火柴的微光中做梦/新年的阳光铺在她的身上时/她有着含笑的嘴角与红颊的脸上/明亮的眼睛不再睁开……”幼年时还稍显朦胧浮泛的感受,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霎时变得清晰真切起来。这首诗尽管读来还相当稚拙——曾卓后来将其另编入《悬崖边的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时,就做过不少修订——可其中寄寓的沉痛哀婉无疑是发自肺腑的。
石兆棠的《大时代之梦》 (蕴山出版社,1946年)在《前言》中就故意调侃道,“忆及如此年岁,什么都可触禁犯法,是否忽然胆敢做梦,也触犯忌讳呢?”为此他赶紧咨询了“‘在民主声中谈法治’的先生们”,幸好“直到目前为止,做梦似属自由,尚无判罚先例”。于是他假托在梦境里遍访古今中西的大哲先贤,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讥刺世相百态。其中一篇《安徒生之答》,虚拟了两人之间的访谈过程。作者直言安徒生把《卖火柴的女儿》写得太美了,“小孩子们只在赞叹那可怜小女儿所见的幻景,而忘怀现实对她的可怕可哀”。虽然安徒生一再替自己辩解,可他还是不依不饶,指责对方“用幻景针对现实来诅咒,那只表现弱者无出路的悲哀”,认为这篇童话脱离现实,充斥着“消极的精神”,而当务之急应该“激发小读者们对社会的正义感,提高他们代表新时代的精神去改造旧的社会秩序”。面对盛气凌人、咄咄相逼的作者,老迈的安徒生只能徒呼奈何,悲叹自己早已落伍,“你们这一代所想的,和我们那一代所想的完全不同”。这场荒唐无稽的对话自然只是借题发挥的小说家言,不能完全信以为真,然而作者将矛头直指《卖火柴的女儿》而不及其余,倒也足以说明这篇童话在读者心目中的显赫地位。

石兆棠《大时代之梦》
苏苏(钟望阳)的童话《雪人》 (载《无名文艺》月刊第一期,1933年)讲述了一个小乞丐在沦落街头时的悲惨遭遇:因为父母双亡,又被送出教养院,衣食无着的他到处受到欺凌。在除夕当天,他无意中误入一座富人的公馆,被发现后遭到毒打,尽管得到同龄的富人之女的同情怜悯,最终还是在雪夜里活活冻死。作品在刊登之初就得到刊物主编叶紫的盛赞,“说是十几年来所少见的” (苏苏《忆叶紫》,载1939年12月20日《上海周报》)。作者随即将作品呈送给一直关心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后者在日记中写有“午后得白兮信并《无名文艺》月刊一本” (《鲁迅日记》1933年6月5日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按:“白兮”即钟望阳的另一笔名),并在回信时表示“很赞同我们的《无名文艺》” (白兮《心中的碑铭》,载《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覆按这篇小说的情节铺陈,其实有许多地方都借鉴了安徒生。比如提到小乞丐闻到从别人家里飘出阵阵肉香,“他看着后门呆立着,忽然那厚厚的门儿变作透明起来了:一盆一盆热气腾腾的美味的肴馔,显在他的面前,他只要一举起手来,便可以尝到那味儿了。但他一提起手来,刚要来拿的时候,他的手触到门上,那里有什么肴馔?”就邯郸学步式地仿照了童话里小女孩在幻觉中看见烧鹅的片段。最后说起冻死的小乞丐在次日清晨成了一个雪人,“在常人看起来,说他定是冻死的,但他自己却不然,他是去打平世界的”。尽管为了迎合时代的需求,把作品主旨改换成了“打平世界,使世界没有穷,没有人欺负人的人”,然而摹拟仿效的痕迹还是一目了然。
包蕾的六幕儿童剧《雪夜梦》 (少年出版社,1946年)最初编写于上海沦陷时期,“以宣传抗战从书店中抄去” (包蕾《我谈儿童剧》,载1947年4月4日《联合晚报》)。等到抗战胜利后,他又做了一番加工润色,添入了“庆祝大胜的游行大队”“雄壮地唱着《胜利进行曲》” (第六幕《寄到上海去的信》)等情节。据作者自述,这部剧作“是受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影响而写成的” (宋国梵编《包蕾作品精选》附《作家传略》,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全剧讲述流浪儿蒂蒂和蓓蓓“在寒风中颤慄着,互相紧挨着,蜷伏在墙之一隅” (序幕《雪夜梦》),凭借仅剩的三根火柴取暖,尔后姐弟俩一起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很有趣很有趣的梦” (尾声《银色的清晨》),其构思确实承袭自安徒生。剧中还特别提到有孩子在生日聚会上讲故事,内容就是“今天在学校里,读到的一课书里面的故事吧!题目叫做‘卖火柴的女儿’” (第二幕《奶油蛋糕的晚上》),藉此细节向童话大师致敬。不过中间六幕剧情均为姐弟俩的梦境,逐一交代他们家破人亡的凄惨身世、手足离散的不幸遭遇、家人重聚的意外惊喜,乃至最终奔赴抗战根据地,参加儿童服务队等曲折经历,虚实交融,亦真亦幻,内容较安徒生原作要丰富许多。作者困居孤岛,目睹种种怪相,时常借剧中人物之口予以辛辣的讽刺抨击。比如蒂蒂曾被一对富商夫妇收养,朝夕相处的生活让她看穿了养父的冷酷投机,“我知道了上海是怎样的地方,住着些怎样的人:有许多人靠着大家的苦难来发财,有许多人在路上饿死,这里有许多失去家乡,没有人管的孩子,也有着每天吃牛奶的狗和猫” (第四幕《小窗里进来的客人》)。不过作者最终依然坚信,“一个新的世界将要造起来了” (第五幕《街头音乐会》),所以并没有因循旧轨让姐弟俩在雪夜中冻毙,而是安排他们在梦醒之后迎来渴盼已久的“大胜利的好消息”,并带领众人齐声高唱“过了冷静的深夜,有着光明的黎明。过了冷酷的冬天,和暖的春天来临。光明的黎明,伴着春天来临。我们迎着春日的朝阳,向着光明前进!” (尾声《银色的清晨》)全剧至此方才缓缓落幕。
陆静山同样以这篇童话为蓝本,创作了一部独幕童话剧《卖火柴的女孩子》 (收入同名童话剧集,永年书局,1948年)。剧中主人公是一个在冬夜里四处奔走叫卖着火柴的小女孩,在街上相继遇到了伤兵、老太太和壮丁。三人都心事重重,步履匆忙,对小女孩兜售的火柴毫无兴趣。然而在转身离开之际,他们又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不约而同都对小女孩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先替她找些食物来充饥。精疲力竭的小女孩瑟缩在墙角,为了取暖,一次次划亮了火柴,眼前先后浮现出自己跟随家人离乡逃难、爸爸被强征入伍当兵、妈妈收拾行李准备返乡等一幕幕幻境。等到伤兵等人带着食物和衣服返回时,小女孩早已冻死在台阶上了。全剧以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为背景,刻画了一幅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众生相:“肚子又饿,身上又寒”的小女孩,“抗战八年受了伤,如今流落在异乡”的伤兵,“抗战牺牲了我的儿子,内战拉去了我的孙子”的老太太,“征光了我的钱和粮,又要拉我去把兵当”的壮丁,这些小人物们辗转流徙、痛不欲生的悲惨境遇,让每一位有着切肤之痛的读者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不过作者并未就此陷入虚无或绝望,不但在剧中反复安排众人合唱“我们不能再受苦难,苦难的人呀要翻身”,剧终时更是强调“远处鸡啼了,天光渐渐发亮,一会就大亮,三人抬起头来迎着阳光”,激励人们对未来寄予希望。长期担任过音乐教师的陆静山编著过大量儿童歌曲,在编著这个剧本时也经常穿插着不同人物的独唱或合唱,最后还附有《卖火柴歌》《要翻身》和《抗战八年胜利到》等歌谱,以供舞台表演时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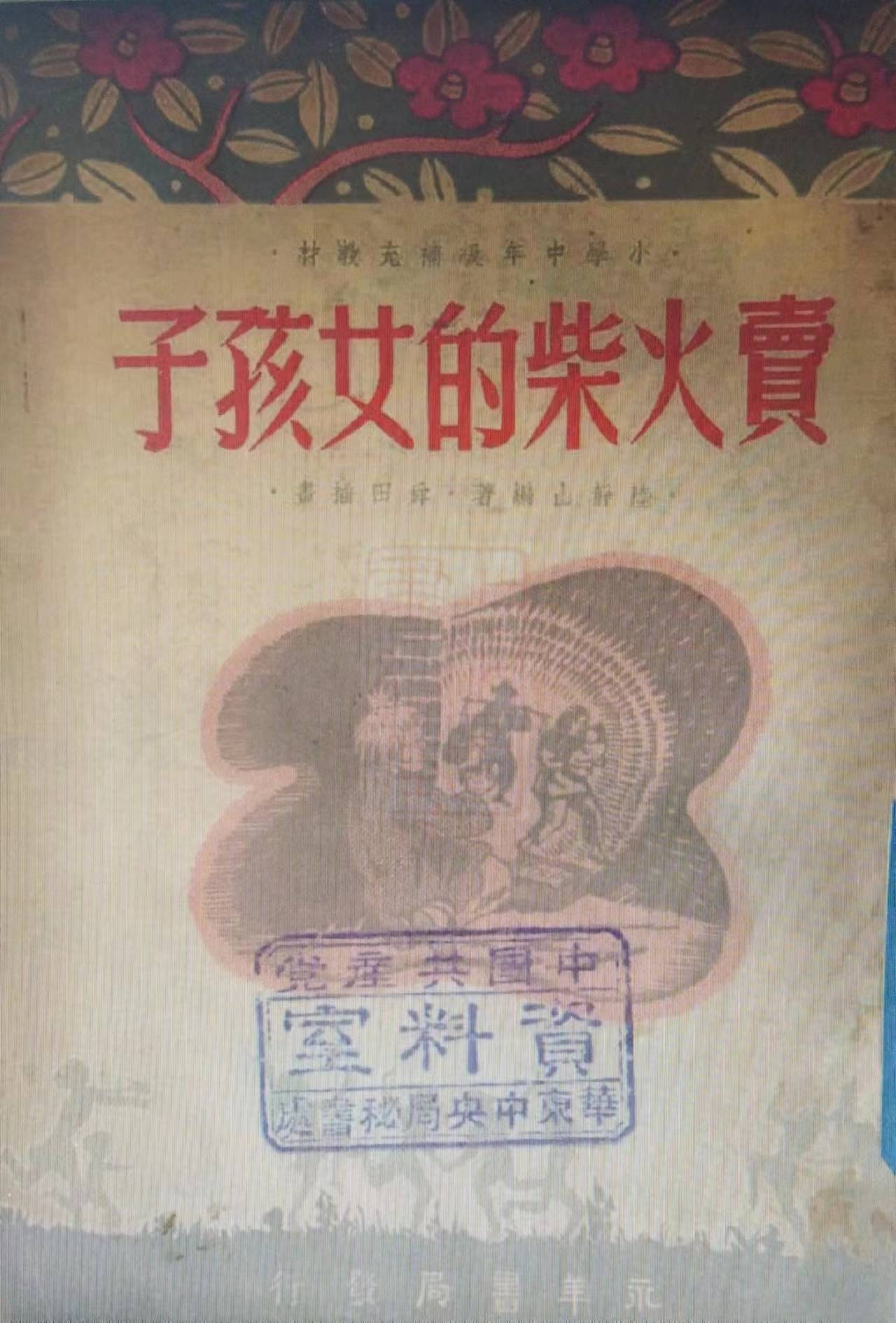
陆静山《卖火柴的女孩子》
直接将这篇童话改编为剧本,并在舞台上搬演的也不乏其例。黄宗英在《我被叶君健吓着了》 (收入《平安家书》,东方出版社,2000年)里提到自己年轻时曾通过广播和舞台,播讲、表演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先是在孤岛时期苏联广播电台的昆仑星期晚会上播讲‘卖火柴的小女孩’;1947年冬,我又在舞台上叙读演饰‘卖火柴的小女孩’”。尤其是那次舞台表演,更是让她记忆犹新,“当大幕在掌声中第三次升起,我想译者叶君健能参加谢幕就好了。我想不出译者什么样儿,也不知他在哪儿……”。有关电台播讲的情况,不免有些语焉不详。确切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3月6日,因为在一周后就有王册的《听昆仑晚会》 (载1949年3月12日《申报》)评论过这次演播,说起“六日晚七时至九时半许,昆仑影片公司一部分主要演员如蓝马、黄晨、吴茵、黄宗英、上官云珠等诸人,假中华自由电台,举行了第二次昆仑晚会”,并称赞道“全部节目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评论者还逐一品评了各档节目,值得注意的是说起“独幕剧一共有三个:《卖火柴的女儿》、《有事化无》和《求仙记》,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冷隽的刻划”。据此可知黄宗英当天播讲的并非安徒生原著,而是据此改编的剧本。至于那次舞台表演,她晚年在《命运断想》 (载《良友》第12辑,文汇出版社,2012年)中还有愈加生动细致的记录,但又说此事发生在“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由于时隔久远,记忆模糊,她两次提到的时间并不一致。据易窕《卖火柴的女儿》 (载1947年11月11日《和平日报》)说,“在戏校的小舞台上看到黄宗英的‘故事表演’:《卖火柴的女儿》”,并为她精湛感人的演技击节称赏,则这次演出当发生在1947年冬,其实比电台播讲还要早。黄宗英回忆起当天登台时,“我赤着脚走上台,走在飘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里,为避风,走向墙边,一直哆嗦地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 (《命运断想》)。所谓“作品原文”必定是根据童话铺展演绎而成的剧本,毕竟原著情节过于简单,人物语言寥寥无几,更没有任何舞台说明,根本无法在舞台表演中直接照搬。而从时间上推断,更绝不可能依照五十年代中后期才问世的叶君健译本。实际上黄宗英对此早有自嘲式的声明,“本人记忆如果与叶君健创作年表不符,无关国计民生” (《我被叶君健吓着了》)。不过这也歪打正着,足以说明叶译本后来居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先前的各家译本以及据此改编的相关作品,否则也不会令当事人出现这样的记忆错觉。
五十年代中后期,叶君健相继编选了两部不同的《安徒生童话选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一部《安徒生童话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又陆续修订完成十六册《安徒生童话全集》 (新文艺出版社,1957-1958年)。然而在随后整整二十年间,这些作品却突然销声匿迹,直至1978年才得以重见天日。而就在这一年,一部根据童话改编的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编剧张敦意,作曲黄安伦,编导邬福康、林莲蓉、黄伯虹,舞美设计郑捷克)也由北京舞蹈学院编排上演。为了使剧作内容更充实,人物形象更丰满,主创人员根据舞台表演的需要做了许多修改增饰。比如在首尾两个场次中增加了一位点灯老人,将小女孩幻想中的祖母改换为妈妈,甚至移花接木,将安徒生另一篇童话《红鞋》中的红舞鞋拿来,作为妈妈送给小女孩的圣诞礼物,让她穿上以后翩翩起舞。两位编导邬福康和黄伯虹总结过编舞时的不少心得,为了让小女孩的三次幻觉富于变化,他们“设计了拟人化的温暖女孩身心的火焰姑娘的舞蹈形象,亲切的、端着烤鹅托盘的小侍者与小女孩的四人Adagio,与善良、慈爱的、给她送来节日礼物的母亲的抒情双人舞和欢快、灵巧的‘红鞋舞’变奏等多色彩的舞蹈手法” (《学习芭蕾舞剧创作的一次实践——谈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收入文化部艺术局、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原本需要借助文字去想象的场景,顿时绚丽多姿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叶君健在看完演出后也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芭蕾舞完全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同时又表达了原作者当时所希望表达的而由于时代局限所未能表达的东西” (《芭蕾舞〈卖火柴的小女孩〉》,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由于这是“第一个打破‘十年动乱’的禁忌,由世界文学名著改编为中国芭蕾舞剧”的作品 (吴晓邦、游惠海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舞蹈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具有特殊的意味,在中国当代舞蹈史上也就成了一部历演不衰的经典之作。

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四、纷歧的评论与隔膜的解读
自诩为“中国的安党” (《随感录(二四)》)的周作人,早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 (载《叒社丛刊》第一期,1913年)中就摘译过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中的片段,推许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在将《卖火柴的女儿》收入《点滴》和《空大鼓》这两部译作集时,他对原先的译者附识做过不少修订,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段评语移植过来,称赞“他用了孩子的眼光,观察事物,写出极自然的童话;一面却用诗人的笔去记述,所以又成了文学上的作品。他之所以为古今无双的童话作家,便只是这缘故”。足见他对这一评价非常认同,而这篇童话更是无可争辩地成了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安徒生代表作。译者附识中还指出这篇作品“又与平常的童话略略不同,所以别有一种特色”,堪称“近世文学中描写冻死的名篇”,其着眼点与他当时尤为注重能够彰显人道主义的平民文学密切相关,透露出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周译本在早期最为风行,这些意见也就随之深入人心。施落英编选北欧小说选集《爱情的面包》 (史特林堡等著,胡适等译,启明书局,1941年),在书前《小引》里说,“全世界儿童爱戴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是人所周知的伟大诗人。本书中所选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窥见作者心情的天真和爱人类的伟大同情”;尔后又在所收录的周译本前插入编选者另拟的《安徒生小传》,指出“他以天真的心情,诗人的笔调,来写童话,所以有很大的成功”,不言而喻都沿袭了周氏的论旨。朱剑芒、陈霭麓编著的《初中国文指导书》第三册 (世界书局,1932年),在解读这篇童话时认为,“雪中卖火柴的女儿,竟没有人怜惜她,这就是社会上一种黑暗的现象”;朱剑芒另行编选的《初中新国文》第三册 (世界书局1937年)根据内容主题分类编排,将周译本归入第十三组“社会上饥寒困苦者的描写”,也同样延续着周氏的思路,从批判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诠解这篇作品的主题。
还有不少学者则继周作人孤明先发之后,分别从思想主旨、语言风貌、艺术技巧等多个层面继续寻绎考索这篇童话的魅力所在。有些见解尽管与周作人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安徒生作品本身则毫无异议,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极高的褒赞称颂。
多次和周作人探讨过童话议题的赵景深对安徒生的作品同样痴迷,其热情程度甚至令同道中人也望而生畏,惊呼“在中国,我们提起了安徒生,大概谁也会联想到赵景深的罢!赵先生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也是出版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的最先的一个” (徐调孚《付印题记》,载赵景深译《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童话集》卷首,开明书店,1930年)。他在《论安徒生童话所表现的人生观》 (载1922年5月3日《天津益世报》)中感喟道,“世间差不多是一个大悲剧场,令人悲伤忧郁的事,真不知有多少”,不过细究其实,“人生的苦闷和痛苦,全系在人的心灵上”,所以不必执着于向外探求解决的途径。安徒生童话更令他认识到寻觅心灵安慰的重要性,“不论你受多大的苦,都可以受安慰,若是你愿意得他。不论你怎样软弱,你若寻着了安慰,自然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做个人了”。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卖火柴的女儿》,但这篇文章经过修订后改题为《安徒生的人生观》,旋即收入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 (新文化书社,1924年),无疑体现了他对安徒生创作的整体评价。在稍后另一篇《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 (载1925年8月16日《文学周报》第186期)中,赵景深继续剖析了“在梦境里求安慰”的实质,认为“悲剧在能自己安慰的人眼光里看来,可以立刻成为喜剧”,“人的境遇虽各有不同,但人的精神,人的心,没有不是一样的具有极大的威权的”。这一次他着重讨论到《卖火柴的女儿》的情节,认为其中屡次出现的“梦的幻境”,足以使女孩“对实生活减少痛苦,减少烦闷,能够再努力的向上走去”。其关注焦点显然已经转向个人精神的净化升华,而不再停留于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
1925年正逢安徒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精心安排了两期“安徒生号”,刊登了一大批译作、评论和参考资料,迅速推动了安徒生童话的传播和研究。他本人特别欣赏安徒生能够运用“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 (《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署名“西谛”),其语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织入一切歌声、图画,和鬼脸在文中”,最终融汇成“新颖有趣”的风貌(《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署名“西谛”)。在编纂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大纲》 (商务印书馆,1927年)时,郑振铎在第三十九章《十九世纪的斯坎德那维亚文学》里也为安徒生留出一席之地,推许“安徒生是北欧最重要、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世界上那一处的孩子,不曾读过他的童话?那一国的文字没有他的童话的几部译本?”令他心驰神往的仍是安徒生“真朴而杰出”的语言,“他并不堆砌美字,并不有意的拣着华贵的辞句写下,然他的文字却于平易素淡之中,自有一种精光,自有一种美彩射出,如素洁的玉,如白色的大理石像,不必假大红大绿以及碎金细银,而自足动人”。他在书中还单独辟出一整页,精心挑选了一幅苏格兰插画家Anne Anderson绘制的《卖火柴的女儿》作为插图,并在图下所配的说明中称,“《卖火柴的女儿》是他童话中的杰作。写一个穷苦的卖火柴的女儿在将冻死于道旁时所见的种种幻象;文笔静穆柔和,而其中乃蕴藏着至深至厚的悲悯”。比起周作人所标举的“辞句简易如小儿言” (《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些感性而细腻的体悟更能具体揭示安徒生童话浑朴醇美的特质。
与鲁迅、周作人昆仲过从颇密的许钦文写过一篇《卖火柴的女儿》 (载《中学生》杂志社编《1931年中学生文艺》,开明书店,1931年),对这篇童话也有不少独到的心得。他提醒读者注意故事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非常有限,可是安徒生却能通过许多细节“顺便补出来历和关系”,而且“用得很巧妙”。比如要表现小女孩日常生活中的衣履残破和丢失鞋子后的茫然无助,“都在写‘脚’底‘红’这点上补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针线细密。他又将小女孩划亮火柴后所见到的不同情景细分为“错觉”“幻觉”和“幻象”三类,“错觉”和“幻觉”都发生在“精神恍惚的时候”而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幻象”源自“不得满足的欲望,精神所受创伤”而与前两者又有性质上的差异。对译者字斟句酌的良苦用心,他也有体贴入微的理解。他发现周译本中有不少长句,诸如“已经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晚上”,“雪片落在美丽的长发——披到两肩的好卷螺发上”,故意把完整的句子“分割开来,而且多用几个字”,这既是为了起到强调的作用,“是着重某一点的写法”,也是因为考虑到儿童的接受程度,“不易领受叠用形容词的语句”。许钦文当时正在浙江省立高中任教,平日写了不少小说,并得到过鲁迅的奖掖提携,能够做出如此细致的分析解读,正是得益于长期以来的教学经历和创作体验。

许钦文译《卖火柴的女儿》
有儿童文学创作、翻译和评论多重经验的李长之曾因为“对于儿童的关切”,而令周作人“印象最深”,“最有同感” (《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载1934年12月8日《大公报》,署名“知堂”)。他在编著《北欧文学》 (商务印书馆,1944年)时设有独立的章节介绍过安徒生,推崇其作品“又不止是年幼无邪的儿童的恩物而已,就是已经失去了童幼的成人也读了爱不忍释” (见该书第二章《丹麦文学》第七节《代表岛屿地带之梦幻的敏感的大童话家安徒生》),倾倒之情溢于言表。在《童话论》 (收入《批评精神》,南方印书局,1943年)一文中,他详细阐述了童话中的情绪表达“往往是起伏而往复的”,犹如诗歌具有节奏和韵脚。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三部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为例,代表“艺术童话”的《卖火柴的女儿》也在其列。他指出故事中的小女孩数次擦亮火柴,就是遵从了“往复和起伏”的规律,“火柴一明一灭,都给小女孩点幸福,幸福马上却消失了,但是最后才是真的永久的幸福”。读者随着这种节奏时忧时喜,可以体验到出乎意料的别样趣味。而童话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特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儿童的天性本来就接近诗,所以“从根本上欢迎重复的韵脚似的叙述的,在他们的创造的探险的心上,是最爱接受起伏的调子的,可以振起他们灵敏的喜悦和恐怖之同情”。他围绕这篇童话的叙事结构及其功能、成因所做的探讨尽管还不够谨严细密,但确实能给读者带来不少启迪和思考。

李长之《童话论》
周作人在《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载《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期,1936年,署名“知堂”)里说起安徒生在西方文学史上也遭受过许多有失公允的指控,“但是,那些批评在中国倒是不会被嫌憎的,因为正宗派在中国始终是占着势力”。他为此忧心忡忡地说道,“安徒生在西洋的命运将来不知如何,若在中国之不大能站得住脚盖可知矣”。随着时移势易,倒真是被他不幸言中,安徒生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内——确实招致了许多非议。正像一位读者观察到的那样,“人们见着它,开始摇起头来,更有人说它只有‘艺术’的美色和香味,却没有实际的教育效益;甚至有人说它的色香会毒害一般年轻的游客” (铮《安徒生童话的教育价值》,载1936年9月16日《申报》)。让人尤为愕然惊诧的是,有些苛责居然来自原先的部分倾慕者。
在刻画小女孩悲惨遭遇之余,安徒生又为她铺排设置了各种美妙的幻象。在许多中国读者心里,这篇童话的主旨就在于暴露黑暗、反映现实,因而对此格外不能容忍。许钦文就批评说,“这只于无可奈何中给死者戴上个花圈,聊以自解自慰,所谓精神胜利,并不是好的办法;我们现在需要实实在在能够使得灵肉一致的平等方法了!”对最为赵景深击节欣赏的“自我安慰”完全嗤之以鼻。朱剑芒等人也提示道,这篇童话的要旨是表现“饥寒交迫的小女儿,虽至冻死而绝无人怜悯”,“至于小女儿临死前所见的种种幻象,那更显然是理想的描写,而绝无这个事实的” (朱剑芒、陈霭麓编著《初中国文指导书》第三册),读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星认为安徒生“在取材上偏重于美的幻梦的空构”,虽然是为了用真、善、美的事物来替孩子们塑造“友爱、和平、自由的人生观”,可是等他们日后踏入社会,幼年美好的幻梦就会被“击得粉碎”,失落怀疑之下必然“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 (《儿童文学的题材》,载《现代父母》第三卷第二期,1935年)。狄福(徐调孚)更是厉声斥责安徒生童话不过是“逃避了现实”的“麻醉品”,“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握住过现实,从未把与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 (《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载《文学》第四卷第一号,1935年)。让人简直难以置信,仅仅数年之前他还在满怀激情地称颂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话创作是“近代的不朽的名著” (《近代名著百种》七《童话全集》,载《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1927年)。面对时局动荡、人事浮沉的残酷现实,终于令许多人对充满幻想的安徒生童话渐渐产生了倦怠乃至拒斥。
童话中描写小女孩憧憬着坐在圣诞树下,最终又让她跟随祖母升入天堂。诸如此类展现宗教情怀的内容在安徒生的作品里并不鲜见,范泉已经嫌其透露出“不切中国国情的宗教色彩” (《安徒生童话集·附记》),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更是不可宽宥地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揭露西方世界的腐朽没落,语文课本里偶尔还会收录这篇童话,却要防微杜渐地告诫学生,圣诞节只是“纪念虚构的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 (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语文》第一册),以防涉世未深的孩子误入歧途。金近也察觉到“安徒生的童话宗教气味很浓厚”,甚至还有不少“抑郁的、消极的成份”,这当然不符合“应该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思想感情”的新时代要求 (《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收入《童话创作及其它》,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他还以本篇为例,强调在安徒生生活的时代因为科学尚未昌明,才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因此不能简单地视其为“向小孩子宣传宗教”。当然,在给孩子们读这些童话之前,“先要做一番选择和指导的工作”。而他对这篇童话的指导意见是,“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女孩》并不是为了宣传人死了可以进天堂,他是为了着重写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的遭遇” (《童话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收入《童话创作及其他》)。在批评的同时还不无回护之意,然而这些煞费苦心的说辞恐怕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吴调公尽管也肯定《卖火柴的女孩》“表现了人民摆脱悲惨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有崇高理想的”,可在例行公事后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由于这理想和‘上帝’混和在一起,因之,小女孩憧憬的——实际也是作者所憧憬的那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就必然是缥缈的、不能实现的境界,而不可能是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这无疑应该归咎于安徒生“受到历史的、阶级的限制而不能反映出高度的真实” (《关于文学的人民性的几个问题》,收入《论文学的真实性和党性》,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这样的作品缺乏“人民性”自然是无可置辩的。
正当安徒生童话遭到口诛笔伐的时候,叶君健也逐渐实现了将其直接从丹麦语翻译成汉语的宏愿。面对自己多年来一直心仪的作家和欣赏的作品,究竟该如何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确实令他踌躇难决。旅欧期间他与诗人贝尔(Julian Bell)、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美学家贝尔(Clive Bell)等诸多“布隆斯伯里学派”成员往来频繁,大家都虔诚地信奉“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及对知识的追求” (叶君健《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收入《欧陆回望》,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这也是促动他下定决心翻译安徒生童话的重要缘由。然而回国以后他就必须抓紧时间脱胎换骨,才能避免在新环境中格格不入。为了纪念安徒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他选译了一部《安徒生童话选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前记》里虽然提到小女孩幻想着升入天堂,实际上却冻死街头,认为“这是安徒生的矛盾。这个矛盾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全文的重点则是竭力表彰安徒生描写了众多“勤劳、勇敢、正直、具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追求光明的人”,强调这些童话作品“不仅鼓励着全世界儿童的向美、向光明追求,同时也能启发成年人”,言辞之间依稀还能看到旅欧时的生活与交游在他思想中所留下的淡淡印迹。
在稍后问世的《童话作家安徒生》 (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里,叶君健的态度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书中再三强调,“安徒生是从穷苦人中来的,所以他切身地体会到穷苦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所受到的委屈和痛苦,因而他知道统治阶级的残忍和没有良心”,“安徒生反对阶级社会的不公平和没有正义。他用极大的同情和爱,描写劳苦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所受的委屈和痛苦”,与时俱进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衡量自己熟悉的作家。此前令学者最称道的是安徒生具有超越阶级的平等观念,“无所谓尊贵、卑贱,大家都是世界上的一个‘人’” (赵景深《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而此刻摇身一变,他居然成了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劳苦大众代言人。叶君健又极为“辩证”地分析道,安徒生创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既是“对于不合理的阶级社会发出严正的抗议”,反映了他“同情广大的劳苦人民”,但也暴露出“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缺陷,“不知道只有通过斗争他们才能走上幸福的道路”。对安徒生热切宣扬的“上帝的‘仁慈’和‘博爱’”,他更是直斥为“一个幻想”,并认为安徒生后来同样“对上帝失去信心”,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以致晚年作品“隐隐染上一层感伤的气氛”。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叶君健都维持着诸如此类的观点,有时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在《鞋匠的儿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中,他就挑剔这篇童话“可能在感情上给读者一定的安慰——也可以说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麻痹。但它却不能说服读者——甚至也不能说服作者本人”,这也就导致作者“产生一种无法解脱的、抑郁的、甚至虚无的情绪”,给他中年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消极、不健康的因素”。到了《芭蕾舞〈卖火柴的小女孩〉》 (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文里,他更是振振有词地说,“在这个童话发表的时候,《共产党宣言》还没有发表”,惋惜安徒生未能在其指引下有所觉醒,不懂得劳苦大众必须紧密团结,“与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得救”。他此前热情颂扬安徒生“热爱我们人的世界、人的智慧和人的创造”,“用丰富的幻想、活泼的语言和真实的感情所写出来的这些诗一般的童话” (《安徒生童话选集·前记》),此时都讳莫如深,被黯然隐去了。

赵景深《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
叶君健晚年一方面继续改订润饰自己的译文,另一方面则尝试做一些评议赏析,来帮助读者理解其思想主旨和艺术特色,而他本人也努力尝试着挣脱思想上的种种禁锢。在《安徒生童话选析》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他精挑细选了十九篇作品,而将《卖火柴的小女孩》列为压阵之作。在该篇所附《简析》中说,安徒生是为了安慰读者才安排小女孩跟随祖母升入天堂,“但这只是一个希望。真正的‘光明和快乐’得自己去创造。上帝是没有的”,语气和措词明显都舒缓婉转了不少。该书《前言》对安徒生作品里屡屡出现的“上帝”还做过一些细致的解读,可供进一步比对参证。他认为安徒生所说的“上帝”其实就是“‘真、善、美’的化身”,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宗教里崇拜的偶像;安徒生非常关心人间疾苦,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再居高临下地斥责批判,更没有阶级斗争之类的僵化教条,而代之以早年令他格外沉醉珍视的“真、善、美”,并用来替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上帝”辩护正名。到了《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里,叶君健对自己的评析又做了大量修改增补。对《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大体维持此前的意见,不过引人瞩目的是,将开篇很简略的一句“这篇童话写于1846年” (《安徒生童话选析》),扩充为“这篇童话发表于1846年的《丹麦大众历书》上”;在最后又迻录了安徒生的一段创作自述,即在旅行途中接到出版商的邀请,“为他的历书写一个故事,以配合其中的三幅画”。关于这篇童话的创作缘由,周作人在翻译时就在篇末识语中根据安徒生“自撰的童话年谱”有过明确交代,稍后张友松还从其自传中摘译过《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不过这些作者自述一直遭后人忽视。叶君健旧事重提,或许未必是刻意之举,但也确实促动读者对前人围绕这篇作品主旨所做的各种诠释加以必要的检讨和反思:安徒生当初是为了满足这一特定需求才创作了这篇童话,又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精心安排在辞旧迎新的那一刻,难道真是意在“揭明贫富阶级底悬殊” (许钦文《卖火柴的女儿》),甚至是为了“对于不合理的阶级社会发出严正的抗议” (叶君健《童话作家安徒生》),抑或“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握住过现实” (徐调孚《丹麦童话家安徒生》)?小女孩最终在街头冻毙,在旁人看来确实悲惨不幸,很容易联想到“其中乃蕴藏着至深至厚的悲悯” (郑振铎《文学大纲》),然而在笃信“仁慈的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万能主宰” (安徒生《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傅光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心中,这样的安排究竟是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对上帝失去信心” (叶君健《童话作家安徒生》),还是另外蕴含着更特殊、更重要的意味?对作品内涵的阐释固然是开放的,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谭献《复堂词录叙》),然而是否就可以反客为主地将读者的理解等同于作者的初衷,乃至心安理得地取而代之?尽管各家对待这篇童话的意见褒贬各异,有时还针锋相对,可是在讨论其创作主旨时似乎殊途同归,都不免未达一间而时有隔膜。赵景深早就慨叹过,“童话家的思想,批评者批评起来,总有些隔膜,很难窥出作者的真意,时时容易发生误会,而思想上的悲乐观念,因为常有互相起落和同时并起的关系,更是容易混淆,难以分出清清楚楚的界限” (《安徒生的人生观》),回想起来,倒还真是一语成谶。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三十九章所配插图及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