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對稱性:楊-米爾斯方程的思想源流與發展丨展卷
- 綜合
- 3年前
- 256
1954年,楊振甯和米爾斯合作發表規範場論的文章,為20世紀後半葉理論物理學的發展開啟了又一個輝煌時代。這一理論延續了物理學四百年來追求的統一思想,從麥克斯韋電磁理論出發,通過對稱性及其所決定的相互作用得出了“力”的規範理論;二三十年後,萬物理論統一的拼圖上擁有了弱電統一模型、量子色動力學,乃至集大成者标準模型,即使後者還不是個自洽的理論。本文介紹了楊-米爾斯方程的思想來源與發展,楊振甯與米爾斯是如何思考的,他們超越時代的思想帶來物理學的進步值得回味。

撰文丨克裡斯蒂娜·薩頓(Christine Sutton)
翻譯丨塗泓 吳俊
校譯丨馮承天
“楊振甯和米爾斯可能走在了他們時代的前面,因為直到約20年後,他們對一個基本原理的信念才結出了碩果,但他們仍還屬于他們的時代。”
紐約的夏天悶熱潮濕,如同無聊的影片。1953 年,斯大林(Stalin)去世了,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Ⅱ)成為英國新加冕的女王,一個年輕的議員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即将迎娶布維爾(Jacqueline Lee Bouvier)。此時,兩個年輕人因共用長島的布魯克黑文實驗室的一間辦公室而相遇了。就像罕見的行星列陣那樣,他們短暫地通過了時空的同一區域。這一時空上的巧合誕生了一個方程,這個方程可構成物理學聖杯——“萬物之理”(theory of everything)——的基礎。
米爾斯(Robert Lawrence Mills)和楊振甯出生得天差地遠,但對理論物理卻擁有同樣的熱情。1953年9月,從中國來到美國的楊振甯31歲,起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然後加盟了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米爾斯當時26歲,是布魯克黑文實驗室新的副研究員,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劍橋大學學習。1953年暑期,楊振甯來布魯克黑文實驗室訪問,當時他和米爾斯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們的研究方向很快分道揚镳,但是楊-米爾斯方程使他們的名字在短暫的相遇後緊密地相連在了一起。
回到20世紀50年代,楊-米爾斯方程似乎是一個有趣的創意的結果,而它和現實卻幾乎沒有什麼瓜葛。不過,在20世紀末,它的時代到來了。它構成了獲1979年和1999年兩項諾貝爾物理學獎成果的基礎,而且在數學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意義,被克雷數學學院稱為七大“千年得獎問題”之一。誰嚴格地解決這一問題,他就能得到1000000美元的獎勵。
為什麼大家都對楊-米爾斯方程感興趣?是什麼使得楊-米爾斯方程如此重要?到底什麼是楊-米爾斯方程?要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物理學家解釋每天我們周圍世界的現象時所用的那些根本性的概念。
對稱的重要性
在用基本的基元構造宇宙時起作用的力中,最為人們所熟悉的力是引力,它在300年前就已在牛頓的數學掌握之中了。其次的便是電磁力,即構成電學和磁學許多方面(從閃電和磁石的自然現象到現代神奇的電視機和收音機)基礎的那個力。還有兩種力,分别稱為弱力和強力。雖然在構成宇宙現存的那些物質中,它們同樣是有作用的,但人們對它們并不那麼熟悉。弱力和強力在原子核(它們位于每一種物質的每一個原子的中心部位)中起着作用。
原子核的這種存在形式乍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帶着相同電性的質子會相互排斥。我們在學校就學過“同性相斥”的道理;原子核内的電場力會完全使它分裂。因為在我們周圍的穩定物質中顯然并沒有發生這種情況,那就一定存在着比電場力更大的力。而這種力隻能在原子核大小的範圍内起作用,否則相鄰的原子會越來越接近,物質就會比現在看到的更稠密。人們把這種在原子核内連接質子和中子的力稱為強力。但這種力起源于什麼?在所有的力中,電磁力是最為物理學家所熟悉的了,那麼強力是否能同樣地被了解呢?正是這個挑戰,激發了楊-米爾斯方程的誕生。
19世紀60年代,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韋成功地把當時關于電學和磁學的所有知識綜合成一套既自洽又優美的簡潔方程組。麥克斯韋方程組,就像牛頓的運動方程一樣,現在仍然在應用。它們給出了計算由電荷或磁場産生的電場以及由電流産生的磁場的方法。這個方程還體現了電磁學裡的一個重要特點:電荷守恒。
電子和正電子通常在同一個地方産生,這一點有着重要的含義。電荷守恒還不僅僅是關于一個大系統的“全局”陳述:“這裡”産生了正電荷, “那裡”就會突然冒出負電荷來達到平衡。它還是涉及時空中從一個位置到另一個位置、從一個瞬間到另一個瞬間的每個點的“局域”陳述。麥克斯韋方程組的一個優美之處就是它們保證了電荷的局域守恒性,而且它們是通過電磁力行為中的固有的對稱性達到這一點的。
楊振甯在麥克斯韋去世近一個世紀後,為了解釋粒子間的強力,他開始考慮是否可以從相反的方向來深入研究。是否可以從一個适當的守恒量出發,用對稱性來發現強力的方程呢?
在數學中,我們說一樣事物是對稱的就是指它在進行某種操作後看上去同原來一樣保持不變,就像正方形旋轉90度或圓旋轉任意角度後同原來一樣。1918年,年輕的德國數學家諾特(Emmy Noether)發現了對稱性和物理量守恒(如電荷守恒)之間有深刻的基本關系。她發現對每一個守恒量來說,都有一個與之相關的對稱性,反之亦然。
既然電荷總是守恒的,那麼諾特定理告訴我們在電磁力中應該有與之相關的對稱性。事實上确實有,而這與某種稱為“勢”的東西有關。“勢”是人們用來表征力場的一種方法,這裡的場可以是電場、引力場或其他的力場。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簡潔的“速記”方法來描述場,這有點類似于二維的等高線地圖比三維地形更簡潔。等高線連接有相同海拔高度的點,等高線越集中的地方,表明該地方的地勢越陡峭。二維的等高線地圖包含了一個有經驗的登山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與此相似,比如說一些電荷的電勢,包括在計算電場時物理學家所需的所有信息,因此也包括在計算這一系統中起着作用的電力時所需的所有信息。
如果我們把電勢說成是與之相關的“電壓”,那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就熟悉它了。小鳥在高壓線上可以和在樹枝上一樣快樂地歌唱。這是因為産生電力的電場取決于電壓差或者說是電勢差。如果我們的整個地球在電勢上升高1000伏,我們的發電廠和電器設備仍然可以運轉如常。要緊的是“火線”和“地線”(“地球”)之間的電壓差值,而不是它們的絕對值。這種“不變性”是全局對稱性的例子:在時空的每一點增加(或減少)相同的勢時,電場是不變的。與此相似,麥克斯韋方程組也不随電勢的全局改變而變化,因此這些方程主要是應對場的問題而不是勢的問題。
然而,麥克斯韋的方程組還包括了要求更嚴的局域不變性或對稱性。電勢在時空的不同點可以改變不同的量,而麥克斯韋的方程組仍舊不變。這就是局域不變性,這一不變性的産生,是因為電荷既構成電場的基礎,也構成磁場的基礎。結果是電勢的局域變化還會引起另一種勢的局域變化,這一勢稱為磁勢。兩種勢的最終變化保證了由麥克斯韋方程組所描述的電場和磁場保持不變,即使當勢的變化是局域的也是如此。麥克斯韋方程組中包含了局域對稱性,而似乎正是這種對稱性才與電荷的守恒有關。
粒子和波
似乎距離了解粒子間的強力還很遙遠,但這裡有一個美妙之處值得注意:我們通過能展示隐藏着的對稱性原理的一組方程,來描述力——這裡指的是電磁力。事實上,它增加了下述可能性:我們看到的物理過程——換言之,我們觀察到的在電和磁之間的相互聯系——是由局域對稱性産生的。這就把我們帶回到楊振甯和米爾斯那裡,他們希望知道能不能從局域不變性原理出發來推導出粒子間強力的方程式。
在麥克斯韋和米爾斯、楊振甯相隔的一個世紀裡,随着量子力學的發展,物理學發生了一場重大的革命。當我們在處理非常小的系統的問題時,牛頓力學不能用了,我們必須使用量子力學。在原子尺度上,我們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粒子的位置和粒子的運動速度。這是因為這一觀測行動會幹擾粒子的運動。我們能通過雷達系統探測汽車對無線電波的反射,來測量汽車通過某一點的速度。此時無線電波的能量很小,它對汽車的運動毫無影響。但要是把汽車換成分子,無線電波的能量将足以推開分子。量子力學論述的是不能同時知道位置和速度(嚴格地說是動量)這一基本問題。這是通過把粒子看成波,并通過在數學上用所謂的波函數描述粒子做到的。波函數與在一個特定的狀态中找到粒子的概率有關。
就像電壓可以升高或降低而它們之間的電場不被改變那樣,波能以某種方式調整,而它的整體效應不被改變。我們改變的波的那部分屬性稱為波的相位。我們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給出了波在其波動的波形中處于什麼地方。當波上升或下降時,固定位置處的波的相位值就會發生變化。對整個波進行一個相位上的改變(即相移)僅僅隻是将整個波形移動了,它不會改變波的一些重要特性,諸如振幅和波長。
同理,描述粒子的波函數也能通過一個固定的相移來變化,而這種相移并不會改變粒子的可觀測行為。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一個全局對稱性起作用的例子。那麼,是不是同麥克斯韋方程組一樣,此時也有局域對稱性呢?假設相移是局域性變化,也即在時空的不同點作不同的變化。在這個局域相移之下,描述粒子的量子力學方程是否也能保持不變呢?
這個問題的直接回答是否定的,因此,似乎我們應該放棄這條思路,而不必為此時的局域對稱性而困擾。然而,要是我們能盡力地修改粒子的方程,使其能不随局域相移而改變,那麼我們就作出了一個重大的發現。隻要粒子在某些力場的影響下發生運動,此時的方程就是不變的。這種情況與電勢的局域改變和磁勢的局域改變之間的聯系有相似之處,隻不過現在講的是在一個粒子相位中的局域變化,它們與粒子在其中運動的場的局域改變有關。當我們意識到電磁場正好提供了對量子力學方程所需要的修正時——隻要我們使對粒子的相移依賴于粒子的電荷即可,那麼上述發現就不尋常了。看來,局域不變性的原理直接揭示了帶電粒子電磁相互作用的本質。
德國數學家外爾(Hermann Weyl)是認識到粒子波函數的局域不變性和電磁理論深層聯系的第一人。他把這種不變性稱為“規範不變性”,因為一開始他想到的是關于尺度(或“規範”)的變化而不是相位的變化。他在1929年發表的經典論文中指出,“對我來說,規範不變性的這一新原理不是來自推測而是來自實驗,它告訴我們電磁場是……物質波場……的一個必然的伴随現象。”
這樣,外爾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提出規範不變性——一個基本的對稱性——可以作為推導電磁學理論的一個原理來用。這在電磁力的情況中是個好主意,但它并沒有帶來新的東西,因為通過麥克斯韋方程組大家早已知道和理解電磁力了。外爾的提議對諸如強力那樣的一個力會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為此時與麥克斯韋方程相應的那些方程仍是未知的。能不能從适當的對稱性原理出發找到這些方程呢?在外爾發表論文的時候,人們還未正确地認識原子核的構成,而且強力的概念也還沒有形成。外爾原理的新應用的時機尚未成熟。
一類新的對稱性
20年以後,這些聯系對稱性和電磁力的深刻構想進入了一個年輕的中國物理學家的腦海。他是來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他叫楊振甯,是一個數學教授的兒子,1945年來到美國。楊振甯在中國時曾讀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傳,因此他就取了富蘭克林這一英文名字——昵稱弗蘭克(Frank)——以表示對富蘭克林的敬意。他最初在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大就讀以及後來在芝加哥的時候,就透徹地研讀了當時頂尖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泡利關于場論的一些評論文章。楊振甯寫到他“對電荷守恒與電磁理論在相位變化下的不變性有關聯的這一思想印象深刻……[并且]對規範不變量決定了所有電磁相互作用這一事實有更深刻的印象”。
楊振甯剛開始時并不知道這些構想來自外爾。當他倆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時,而且甚至偶然碰面時,他也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外爾在1933年離開德國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職,于1939年成為美國公民,而1949年時楊振甯也在該研究所。外爾是在1955年逝世的,看來他很可能并不知道楊振甯和米爾斯所撰寫的出色論文——這篇文章第一次闡述了規範不變性的對稱性事實上是能确定基本力的行為的。
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楊振甯着手把這些構想運用到粒子的另一個特性之中,和電荷一樣,在粒子的相互作用中這個性質也是守恒的。他志在尋找描述與這一特性的規範不變性相聯系的那個場的方程,這種特性有一個相當容易搞錯的名字叫“同位旋”。同位旋像一個品名标簽,它标志出了除電荷不同以外,其他都顯得同樣的那些粒子。設想有一對雙胞胎彼得(Peter)和保羅(Paul),除了其中一人穿了件外套以外,他倆打扮相同。脫下這件外套,他們就變得難以區分了,雖然他們仍有不同的名字。對于粒子也有同樣的情況,如質子和中子,質子穿了件正電荷的“外套”,而中子“沒穿外套”,也就是不帶電。20世紀30年代,人們對原子核的研究揭示了:一旦不計不同電荷所造成的差異——一旦質子脫下虛構的電荷“外套”——那麼中子和質子、中子和中子、質子和質子,都以相同的方式相互作用。換言之,粒子間的另一個力——強力——将不會發現上述3種情況之間的差異。質量非常接近的質子和中子,對強力來說顯示為同一個粒子“核子”的兩個狀态;正像我們用名字來區别雙胞胎那樣,我們現在就用同位旋的數值來區分這些粒子了。這種情形類似于粒子處于稱之為“自旋”的那一量子特性的各種不同狀态之中,而描述粒子自旋狀态的數學就能用來表述同位旋狀态。
從數學上來說,你能“旋轉”質子的同位旋使其變成一個中子,而此時作用于該粒子的強力效應不會改變。于是在力中有了一個對稱性,正如諾特定理告訴我們的,某樣東西必定是守恒的;而它就是同位旋。現在,我們已擁有拼成楊-米爾斯方程的所有片段了。
一種新的場
從1949年開始,楊振甯多次嘗試把電磁力中的規範不變性過程運用到同位旋中去。但是據楊振甯所說,這些嘗試總使他陷入“困境”,困于計算中的同一步驟,這種情況總發生在當他要定義相關的場強時。但他從來沒有完全退縮過。正如他在他的《論文選集》中解釋的,“這種在某些看來是美妙的思想中的反複失敗,對所有的研究工作者來說都是家常便飯。大部分這種思想最終會被摒棄或被束之高閣。但一些人會堅持并開始着迷。有時一種迷戀最後确實會變成好事。”尤其當時人們在實驗中發現了許多短壽命粒子,而關于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力,似乎有同樣多的構想出現。對楊振甯來說,“寫出[這些]相互作用的原理的必要性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了”。
1953年夏天,楊振甯在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時又一次思考這些問題,而此時和他在同一個辦公室的年輕物理學家米爾斯也被這些問題迷住了。他們共同越過了楊振甯早期遇到的障礙,從而發現了與同位旋規範對稱性相聯系的那個場的方程。
如果我們忽略電磁作用,那麼我們把什麼粒子叫質子,什麼粒子叫中子的選擇就變得随意了——把所有的中子變成質子或反過來把所有的質子變成中子,核反應還是相同的。這就相當于在同位旋狀态中作了一個全局改變——我們在時空中的所有點上以同樣的量“旋轉”了同位旋,以緻使所有的質子變成中子,所有的中子變成質子。不過,楊振甯和米爾斯問道,如果我們在時空中的不同點進行不同的變化,那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正如他們在論文中所說的,假定兩個同位旋狀态之間的“旋轉”是完全随意的,或“沒有物理意義的”,這正像在帶電粒子波函數中任意的相移,它能被電磁場的變化所補償。那麼是否有一個場,能類似地補償同位旋的局域變化并保證核反應看上去總是相同的呢?就其本質而言,同位旋理論的證明要比電磁理論複雜得多。為了保持質子或中子在各處都有同樣的本體,補償的場一定要能校正同位旋中的局域變化或“旋轉”。為此,該場本身也必須有同位旋的性質。與之相反,在電磁力中,粒子波函數的局域變化并不改變粒子的電荷。電磁場不改變電荷的這一事實就反映了這一點。電荷可以被定義為電磁場之源,但是電磁場本身卻不是電荷之源。然而,在楊-米爾斯理論中,這個場卻以一種聽起來使人有過分親密關系的感覺,它就是其自身之源。
楊-米爾斯方程就是這個場的運動方程。它相當于麥克斯韋方程組或牛頓運動方程,且能以相似的方式寫下來。采用楊振甯和米爾斯當時使用的符号來表示,這個方程可寫成:

這裡f代表楊-米爾斯場的強度,∂/∂xν表示方程與場強随空間和時間變化的關系;ε 有“荷”的作用,而Jμ表示相關的流;bν是該場的勢。(bν× fμν)這一項表示了與電磁情況最重要的差别,因為它帶來楊-米爾斯場對自身的依賴性。在麥克斯韋電磁方程組中,相應的這一項等于零,因為此時的基本場之間彼此沒有影響。
質量問題
楊振甯和米爾斯發現的新的場還有一個重大障礙,它是關于“場粒子”的。在楊振甯和米爾斯作研究用的理論框架——場的量子理論之中,場是由粒子來表現的。這些“場粒子”不僅是描述場的一種簡便的數學方式,在某些情況下,它們還作為一些可測的實體,如同電子或質子一樣真實,在場中出現。在電磁理論中,場粒子是光子,它們從電磁場裡出現,以光的形式為我們所見。
在相互作用着的“物質粒子”(例如電子和質子)之間進行的一場“量子接球遊戲”之中,場粒子起着球的作用。在電磁的情況中,帶電粒子是通過投和接光子來玩“接球遊戲”的。光子沒有質量,因此這種相互作用可以發生在相距很遠處,原則上講是無限遠(你可以想象把光子“球”扔到無限遠)。相反,質子、中子間的強力作用範圍卻似乎限制在原子核的尺度裡。這意味着,強力的“球”必定有一定的質量,以保證這種交換——這種相互作用——總是在有限的時間裡發生的,也即有一個很短的距離。
楊振甯和米爾斯發現的新場在空間和時間中的每一點按要求校正同位旋,把質子變成中子,中子變質子或讓它們保持原樣。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3個傳遞粒子,它們是同位旋的3個狀态。這個場也能改變電荷,例如從帶正電的質子到不帶電荷的中子。所以其中兩個傳遞粒子必須帶有正電荷和負電荷,而第三個保持中性并參與質子與質子或中子與中子的相互作用。因此楊振甯和米爾斯知道了新場粒子的電荷和同位旋,但他們對它們的質量卻沒有任何概念。他們認識到這是其理論中的一個薄弱環節。1954年2月,楊振甯在普林斯頓的一次研讨會上提出他的理論,他發現自己受到了泡利的抨擊。楊振甯在黑闆上剛寫下他的新發現的場的表達式時,泡利就問:“這個場的質量是多少?”楊振甯解釋說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他和米爾斯還沒有得到明确的結論後,泡利尖刻地指出“這作為理由是不充分的”。
雖然到了 1954 年 2月楊振甯和米爾斯已經完成了工作的絕大部分,但對是否發表一篇論文仍然猶豫不決。正如楊振甯所寫的,“這個構想是優美的,它應該發表。但規範粒子的質量是什麼?我們沒有肯定的答案,隻有一些令人沮喪的經曆告訴我們[這個]問題比電磁力要令人困惑得多。我們根據物理學上的一些理由,往往會認為帶電荷的規範粒子不會是無質量的”。楊振甯本人強調突出“優美”一詞,看來優美戰勝了疑惑。1954年6月底,他和米爾斯向著名期刊《物理學評論》投遞了論文,這篇文章在三個月後的10月1日發表了。在文章的倒數第二段的結尾處,他們遺憾地指出他們“還沒有能得出關于b量子之質量的任何結論”。這裡的b量子,換言之就是他們新場的傳遞粒子。
電弱統一
對基本粒子和力的理解的不斷進步,就像任何一門學科那樣,是在構想和發現——理論和實驗——的相互促進中實現的。就像樂器的二重奏,兩者相互補充,有時是這一個主導,有時是另一個主導。有時一個樂器要試奏出一些斷斷續續的新曲段,而另一個卻繼續演奏原來的主旋律。再過一會兒,某一個曲段會變成主旋律。與之相似,物理學家用理論的思維和實驗的研究來探索不同的道路。一些被證明是不會有結果的而且被遺忘了,而另一些會在晚一些的時候重新回來引導我們的認知。楊-米爾斯方法對我們認識強力的神秘作用起先可能沒有提供什麼洞見,但它如今卻是我們理解各種粒子和力的基礎。然而,隻有經過理論上的進一步發展和實驗的不斷發現,我們才真正清楚楊-米爾斯方法和粒子間力的性質之間的關聯有多大。
1979年10月,在楊-米爾斯論文發表25年以後,三個理論物理學家從斯德哥爾摩獲悉他們被授予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格拉肖(Shel⁃don Glashow)、薩拉姆(Abdus Salam)和溫伯格(Steven Weinberg)三人各自獨立地在局域不變性原理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他們之前的楊-米爾斯構想和外爾構想的時代到來了,但卻是以一種相當意想不到的方式到來的。
新的理論把電磁力和弱力放在一起考慮,而不是考慮按楊振甯和米爾斯所遵循的思路那樣可能得出的電磁力和強力。“電弱理論”還成功地解決了質量問題并且納入了重場粒子。不僅如此,這個理論(在一些能被測量的量的少許幫助之下)甚至還預言了這些粒子的質量。
弱力是某些種類的放射性的基礎。發生這種放射時,原子核所包含的中子變成質子,或反過來,這樣原子核就“衰變”了。這些過程引起了真正的煉金術,因為它們改變了核中質子的數量,而這又依次改變了該原子核所屬的原子的化學性質。碳能變成氮,鉛能變成铋,等等。與此相似,在太陽和其他恒星的核心中,質子在核反應鍊中變成中子并釋放出能量。所以雖然弱力在原子核裡比強力小100 000倍,但是它對我們宇宙的性質,以及通過太陽對生命本身産生了非常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就日常世界上的現象來說,電磁力和弱力竟然會在根本上緊密地相連在一起,這似乎使人驚訝不已。電和磁的長程作用是宏觀的大尺度現象,諸如雷暴雨和北極光,而弱力的作用則是隐秘的,處于微觀的亞原子尺度。我們獲取的來自太陽的生命能源是以光子——電磁場粒子——的形式到來的,盡管這一能量是在太陽核心深處,在核的弱相互作用所引發的反應中釋放出來的。格拉肖、薩拉姆、溫伯格正是在這些看似無關的現象中發現了它們之間的聯系,雖然這是一個他們最初都沒有打算着手去作出的發現。
在英國,薩拉姆對用局域不變性來理解粒子間的弱力很感興趣。弱力能改變粒子的電荷,例如把中子變成質子。因此,薩拉姆提出弱力可能來自像楊振甯和米爾斯所描繪的那樣一個場,這個場有三種“場粒子”分别帶正電荷、負電荷和零電荷。正場粒子和負場粒子可與改變電荷的弱相互作用很容易地聯系起來,但中性場粒子卻更成問題。一種自然的選擇是把它和一種熟知的中性場粒子——電磁學中的光子——等同起來。這樣,“電弱統一”的構想就開始在薩拉姆的腦海中形成了。
在美國,格拉肖在研究一個類似的課題,盡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現存的一些弱力理論總是會導緻在計算中出現沒有物理意義的無窮大量。他認為通過把電磁力和弱力納入到一個理論中,計算中那個令人不知所措的無窮大問題就能得到解決。他選擇把他的嘗試建立在楊-米爾斯方法上,并且和薩拉姆一樣,假設其中的中性粒子是電磁學中的光子。然而,格拉肖和薩拉姆各自很快地認識到有一個更好的理論,這個理論以不同的方式把電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對稱性并合起來。他們的結果是有兩個中性場粒子的一個理論。這兩個場粒子是電磁學中的光子和弱場中的一個不同的中性粒子。
這個理論剛開始有好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就是質量問題,這個問題以前曾給楊振甯和米爾斯帶來了許多困難。與強力相比,弱力的作用範圍顯得很小,這意味着在“量子接球遊戲”中的弱“球”一定很重。在此電弱理論中,光子還是沒有質量的,但弱場的正粒子、負粒子和中性粒子都有很大的質量。但是賦予場粒子以質量會破壞局域不變性,而若是這樣,這種方法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依據了。更使格拉肖灰心的是,無窮大問題仍然存在,而且關鍵是并沒有實驗表明存在着這個理論所要求的那個重的中性場粒子。
質量難題的解決來自于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一個完全不同的物理學領域,它研究的是固體中原子的集體行為。關鍵在于下列概念:即使作為基礎的方程是對稱的,物理系統仍可以存在于一個缺乏對稱的狀态之中。例如,鐵原子能表現得像小磁體。在一塊普通的鐵中,這些原子磁體指向是随機的,因此有對稱性,因為沒有一個方向比任意其他方向更占優勢。但是鐵能被磁化,此時原子磁體按磁場方向排列起來。原有的對稱性似乎消失了,雖然描述原子運動的方程還保持它們原有的對稱性。好幾個理論物理學家,其中有愛丁堡大學的希格斯(Peter Higgs),意識到他們能運用這些觀點使粒子獲得質量。這隻要在方程中引入另一個場——這個場現在叫希格斯場。
希格斯場是不尋常的,因為雖然與它相關的勢是對稱的,但在該場中的運動方程的解卻是不對稱的。實際上希格斯勢就像酒瓶凹陷的瓶底——整體形狀是對稱的,但是在凹陷頂端瞬間平衡的一粒豌豆會向一個方向滾動,這樣就打破了對稱。描述粒子間相互作用的方程蘊含着這樣的意思,即粒子就像凹陷頂端的那顆豌豆——在最初的理論中,它們沒有質量,但當它們與希格斯場作用時,它們就打破了對稱性并獲得了質量。
美國的溫伯格看到了在楊-米爾斯理論中運用對稱破缺的構想來描述強相互作用的希望。一開始他并沒有成功,因為他試圖将他理論中質量巨大的和無質量的場粒子跟已知的強作用粒子等同起來。他在接受諾貝爾獎金時的演說中回憶,“1967年秋天的某一天,在驅車去麻省理工學院辦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想到我把正确的構想用到一個錯誤的問題上了。”他意識到他需要的無質量的粒子是光子,而質量巨大的粒子是弱場粒子。“于是弱相互作用與電磁相互作用就能以一種确切的,但是自發規範對稱破缺的方式,來統一地加以描述了。”
4年後的1971年,理論最後潤色完成了,這使得“溫伯格-薩拉姆-[格拉肖]的青蛙變成了一位被魔法迷住的王子”——科爾曼(Sidney Coleman)的這一說法使人浮想聯翩。在荷蘭的烏德勒支,特霍夫特(Gerard 't Hooft)和韋爾特曼(Martin Veltman)一起工作,他們證明了在一個被稱為“重正化”的過程中,該理論中出現的一些無窮大抵消掉了。現在格拉肖明白他早期的難題是如何解決的了。“在重正化性的研究中,”他寫道,“我勤奮地工作但錯過了機會。規範對稱性是一個精确的對稱性,但它是隐藏着的。我們不能用人為的辦法把質量項加進去”(像他曾做的那樣)。特霍夫特和韋爾特曼的工作使電弱統一的處理方式上升到一個極為可敬的理論,而在 1999 年,人們确認了他們使電弱“青蛙”在衆多理論中變成了王子的工作,他倆被授予諾貝爾獎。1973年到1983年的這10年裡,許多關鍵的要素齊備了。1973年,實驗最初揭示了“弱中性流”。這些隐約存在的過去未觀察到的反應,揭示了存在着弱力的重中性場粒子。1983 年,帶電的和中性的弱場粒子在高能碰撞中被人為産生并被探測到了,而它們的質量與用電弱理論計算得出的結果一緻。這是對楊-米爾斯基本觀點一次激動人心的肯定。
“色力”
關于弱力和電磁力的所有這些進展,是在何處脫離了強力——那個楊振甯和米爾斯曾一直想要描述的力的?20 世紀 60 年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許可以把這10年看成是與一些陳舊觀念決裂的10年——其中相當重要的是,我們對基本粒子實際上是什麼這一認知改變了。人們發現質子、中子和大量的短命粒子是由更基本的粒子構成的,我們把它們稱為誇克。例如說,每個中子和質子都由 3 個誇克構成,它們由強力結合起來。當時已經清楚的是,誇克的某些性質決定了強力。
理論物理學家開始認識到要使3個相同的誇克形成一個類似質子的粒子,這些誇克就必須帶有一個新的、可予以識别的特性。為了滿足量子理論的定則,這個特性必定要能區分出在此以外完全相同的誇克。類似于光的三原色,人們把這個能取3個值的特性稱為“色”,而其可能值就用紅、綠、藍來表示。重要的是,人們逐漸搞清楚了不是同位旋而是色才是“強荷”——誇克之間的強相互作用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學家為色誇克構造起來的理論正是楊振甯和米爾斯早已探索的那一類型理論。但是,因為色有3個值,而不是楊振甯和米爾斯所考慮過的同位旋2個值,因此此時得出的場就更為複雜了。此時應有8個場粒子而不隻是3個。這些場粒子稱為膠子,而且像誇克那樣,它們也必須是帶色的,這樣才能使得這個滿足局域不變性的新場是一個楊-米爾斯場——它是自身之源。這個描述來自“色荷”的強場理論被稱為量子色動力學(簡稱QCD),類似于我們論述電磁力的量子理論,即量子電動力學(簡稱QED)。結果表明QCD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理論,那麼它是如何解決對短程強力所預期的重場粒子的那個問題的呢?
其答案就在膠子之間所能發生的相互作用的複雜性之中——這一特性在具有不帶電的光子的 QED 中是完全不會産生的。QCD 内的膠子相互作用使“強荷”——例如說一個紅誇克——周圍的力的有效強度在短距離内減少。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因為兩百年來物理學家一直認為,當你靠近電荷時電荷的作用力會增加。但是,這個新效應似乎能解釋20世紀70年代早期做出的一些似非而是的實驗觀察結果,這些實驗是用高能電子去探測質子和中子。這些實驗發現,當電子探測到更小的距離時,它們開始與原子核裡的誇克相互作用,仿佛它們是完全自由的,或者說在更大的實體中根本沒有受到束縛。(譯者注:舉例來說,電子對質子的“深度”非彈性散射的實驗結果是:質子是由3個幾乎自由的點狀帶電粒子,即誇克構成的。)這一結果與強力随着距離的縮短而變弱的觀點是吻合的。
那麼距離增加後會發生什麼呢?強力似乎會變得更強。這個結論似乎提示單一的誇克不能像電子能被撞出原子一樣從質子或中子中彈出,當然,從來沒有證據表明能觀察到單一的誇克。因此,強力的作用範圍似乎是很小的:誇克被幽禁在那些粒子的範圍内。由此推出,為了解釋強力的短程性,就毫無必要要求膠子是很重的。QCD中的膠子仍是無質量的,因此對該理論的局域對稱性來說也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作者簡介 斯蒂娜·薩頓(Christine Sutton),粒子物理學家,曾在牛津大學粒子物理研究組工作, 2003—2015年擔任《歐洲原子核研究中心快報》(CERN Courier)主編,擁有豐富的科學寫作經驗,著有《粒子奧德賽》(The article Odyssey)等。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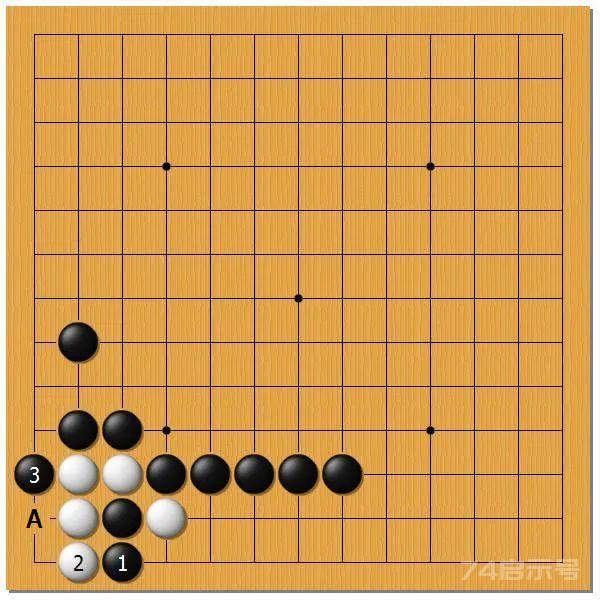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