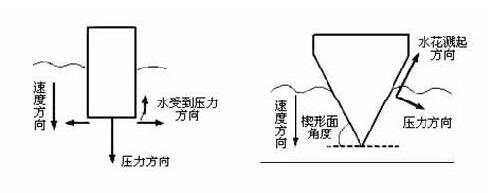上外教授谈翻译:比找老婆还难!
- 文化
- 2天前
- 199
如今翻译活动可谓十分普遍,不论是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各类国外文学作品、科技著作,还是工作中屡屡接触到的国外信息,甚至号称“第一大专业”的外语专业,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世界接轨,翻译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个时候,我们正本溯源,对翻译的定义做一番探讨,似乎很有必要。
世界不同民族为了能够交流思想,进行交往,就需要通过翻译沟通。老生常谈了:翻译是什么?西方人幽默,好出惊人之语。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名言云:“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得得,搞翻译成了找老婆,既要贞洁又要漂亮。而这谈何容易?这个比喻明显有绝对化的倾向,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也含有对女性的不尊重。世界上漂亮而又对爱情专一的女人多的是。同样,忠实于原文而又文笔流畅优美的上乘译作也大量存在。但是,确实也要防止这样的现象:译文妙笔生花,词句华美,然而却经不起与原文的核对。就翻译而言,漂亮与忠诚两个要求都应达到。又云:“翻译即叛逆”?“翻译是误解的总和”,喏喏,翻译又成了叛徒,还必须以错为对信口雌黄,对的匪夷所思。世界上的翻译活动也不会因此而中止或取消。好的翻译应当被看成是与原作“喜结良缘”,只有那些不负责任的翻译,那种劣质译文才是对原文的粗暴践踏(何刚强,2003:11)。
相比之下,还是国人说的一听就明白。如一代翻译宗师傅雷先生自嘲翻译乃“舌人”。也就是说翻译就是鹦鹉学舌,须巧舌如簧唯妙唯肖——“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创作”。翻译名家杨绛女士则称“翻译是一仆二主”(2005年3月23日《中华读书报》),译者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读者”。这说明翻译活儿并不好干,弄不好两头受气。说来说去,翻译究竟是什么?
有人会说,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书谈到了,没有必要再多谈了。其实不然,做任何一件工作,先要弄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工作。从事翻译研究或实践,当然也要至少从基本理论和实际意义上弄清楚翻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外语言学家给“翻译”下过不少定义,表述有繁有简,但基本内容比较一致。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一书中写道(丁树德,2005:2):“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给翻译下的定义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一些书中把翻译定义为“用译语语篇传达原语语篇的信息,以实现原语语篇及译者的交际目的”(李运兴,1998:1)或“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等,1983:绪论)。还有的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柯平,1993:7)。
但是,比较而言,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Nida)的翻译定义较上述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翻译即译意( means the )。”就实质而言,翻译即译意。但就方法而言,翻译即意译(张经浩,1996:7)。对此,奈达先生还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in in the the of the , first in terms of , and in terms of style)。”(Nida, A. & Taber, C.,1982:12)奈达的表达为译界更多人士所接受,因为这一定义说明了翻译的实质:第一,翻译中人们要译的是信息()。奈达把翻译的逻辑重点放在了“再现原语信息”上;物质、能源、信息是当代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三者是流动的。在信息流动中,翻译的功能在于“再现原语信息”。 第二,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原文和译文只能是最贴切()的对等。奈达所说的“最贴切”是对原文内容而言的,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第三,译文是最自然()的对等。“最自然”是就译语而言,即要使译语读者感到自然通达。这样,才能使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达到等效。
由此可见,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既是一种语言活动,又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同时运用两种语言表达思维内容的活动。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它兼有艺术和科学的双重特征:
一方面,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译文要再现原文风貌,必须经过判断、推理、演绎、归纳、抽象、升华等一系列思维创造过程,而这种再现就是一种艺术。翻译的艺术性又在于适度,学会甘受局限和忠于原作的意图,是翻译艺术中最难学的东西。如果把创作比成自由跳舞,翻译就是戴着手铐脚镣在跳舞,而且还要跳得优美(冯庆华,1997:1)。因为创作不受语言形式的限制,而翻译既要考虑到对原文的忠实,又要按照译文的语言规则来表达原文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并不比创作容易,有时甚至更难。鲁迅先生在述及翻译甘苦时说过(黄新渠,1998:1):“我向来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需构思,但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鲁迅先生此语已成国内译界的一句名言。它从一个侧面说明翻译之难。“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1853-1921)的这两句话道出了翻译的艰难程度。为了译好某个词,译者竟花费十天半月的时间潜心琢磨。这些深切的体会都说明优秀的翻译是一门艺术,就像画家用画笔把画的人物的形状和神态再现在画面上。
另一方面,翻译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不受译者意志的支配,而是受着诸如语法、修辞等规则的制约。翻译是一种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的活动,并且可以与各门不同的学科进行富有意义的联系。翻译也是一种技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翻译的具体方法是可以传授的,而且人们做好翻译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大大提高的。同时,翻译又是一种文化活动,如同阅读、写作一样。进而言之,翻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实践性强的文化交流活动。
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翻译都离不开实践。翻译就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信息、情感、思想、文化的交流。翻译要否理论指导,也许至今仍然众说不一。那么,译者究竟是如何进行翻译的呢?对于这个看似简单却倍受关注的问题,回答起来似乎又是难以捉摸的。西方一位文学翻译家这样写道(, 1989:117):
If asks me how I , I am hard put to find an . I can the . I make a very rapid first draft, put it aside for a while, then go over it at a slow pace, – and – in hand. But that is all . the job is .(若问我怎样做翻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可以描绘其实际过程:首先迅速草拟一份译稿,将它搁置一旁片刻,之后是手执铅笔橡皮进行一段痛苦而缓慢的仔细检查、润色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内在的情形却是无限复杂的。)
以上引文中的“ ”(无限复杂)与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的“聪颖者”之说可谓不谋而合(, 1969:85):
“… Any old fool can learn a … but it takes an to a ”(任何傻瓜都能学会一门语言,但是要想成为一名译员非聪颖者莫属。)
有人认为,翻译家不一定谙熟翻译理论,翻译能力全靠在实践中培养提高。此论固然有一定道理,却未免有失偏颇。翻译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科学。科学是有原理指导的。即使是技能,也有其理论根据。施展区区小技也离不开若干科学原理的指导。译作的成功,不一定是译者探索翻译科学的结果,而成功的译作却一定符合翻译的客观规律,一定反映了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两种语言的纯熟运用,其成功之处完全可以用翻译科学加以解释,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这样做过。因此,翻译既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或机械式的替代过程,也不是毫无理论根据,毫无章法可循的纯粹的经验活动。翻译需要创作,但不能越矩。创作即是艺术,即是科学。
综上所述,当今翻译界对翻译的定义虽然版本多样,核心内容却不离其“宗”: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通过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让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相互了解,彼此沟通。翻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变化万千,需要个人创造力的艺术。尤金·奈达也赞同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提法(Nida, A. & Taber, C.,1992:132):
“ is far more than a . It is also a skill, and at the , fully is an art.(翻译远不止是一种科学,它还是一种技巧,而且说到底,完美的翻译永远是一种艺术)。”
本文摘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传媒新词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