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世30年,她仍是這個時代的傳奇
- 文化
- 3年前
- 265
1973年,地球的另一端,被遺忘的西撒哈拉沙漠裡,走進了一個中國女人。
她中分着一頭漆黑的長發,穿一條波西米亞花長裙,拖着不多的行李:一隻大箱子,一個大背包,一個枕頭套。
她就這樣呆呆地立在天高地闊的黃沙邊緣,定住了,像是被大沙漠攝去了魂。

▲那個義無反顧地走進沙漠中的女人。
此後三年,她在沙漠中度過了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寫下一個個浪漫傳奇的撒哈拉故事。
這個終其一生都帶着“撒哈拉沙漠”印記的中國女人,名字叫三毛。
前世的鄉愁 鋪展在眼前啊
一疋黃沙萬丈的布
當我當我
被這天地玄黃 牢牢捆住
漂流的心
在這裡慢慢慢慢 一同落塵
呼嘯長空的風 卷去了不回的路
大地就這麼交出了 它的秘密

三毛在不叫三毛之前,叫陳懋平。三歲學寫字時,因為覺得“懋”字筆畫太多,她就自作主張省去了,管自己叫陳平。
“平”是“和平”的平,寄予了戰火歲月中一對平常夫婦對自己孩兒最樸素真誠的盼想。
1943年3月26日,三毛出生在重慶。
那個年頭,中國的抗日戰争還沒有終結的迹象,她就出生在父母親從浙江避難到重慶的時期。
“三毛,不足月的孩子,從小便顯得精靈、倔強、任性。話雖不多,卻喜歡發問;喜歡書本、農作物,不愛洋娃娃、新衣裳。可以不哭不鬧,默默獨處。不允許同伴捏螞蟻。蘋果挂在樹上,她問:是不是很痛苦?”(陳嗣慶《我家老二》)
還在根本不認得幾個字的階段,三毛就喜歡上了書本。

▲小時候的三毛有一點可愛。
她最愛圖畫書,很早就“玩”過了《木偶奇遇記》《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集》《愛的教育》《愛麗絲漫遊仙境》等童話故事書。
在這些圖畫書中,她最喜歡《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
小小年紀的她,看這書時,為着頭上隻有三根毛發的可憐流浪兒,有時流出眼淚,有時酸澀一笑。小時候埋下的執念,使得她人過中年後專程去拜訪了漫畫書的作者張樂平,了卻夙願。
認字以後,她對書本的喜好有增無減,最愛讀各種課外書。
她自稱一生好讀《紅樓夢》,在小學課堂上,還會把《紅樓夢》藏在裙子下面偷偷地讀。用她自己的話說:
讀到了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詳說太虛情,賈雨村歸結紅樓夢”……當我看完這一段時,我擡起頭來,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學的背,我呆在那兒,忘了身在何處,心裡的滋味,已不是流淚和感動所能形容,我癡癡地坐着,癡癡地聽着,好似老師在很遠的地方叫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沒有回答她。老師居然也沒有罵我,上來摸摸我的前額,問我:“是不是不舒服?”我默默地搖頭,看着她,恍惚地對她一笑。那一剎那間,我頓然領悟,什麼叫做“境界”,我終于懂了。
六歲時,三毛跟随家人從大陸去了台灣,在台北國民小學念的書,後來升入了台北省立女中(即後來的北一女中)。

▲三毛曾經讀書的地方。
在那裡,她面臨着人生中第一個轉折點。
由于癡迷古今中外各種故事書,三毛的成績非常一般,數學尤其不好,簡單的雞兔同籠也沒能弄明白。
在父母親的勸告下,勉強收了心,每一門課都認真地背,每道數學題都背,終于考了六次數學滿分,不料卻遭到了數學老師的懷疑。
據她回憶,從國小畢業後,她進入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七年:
“13歲時我在北一女中念初二,數學月考我考了好幾次100分,老師不相信,又出了一次我完全不會的方程式,當然我就考了零分。然後老師就處罰我,她用毛筆在我眼睛周圍畫了兩個大圈,墨水太多,流到唇邊,她就要我這個樣子到操場繞場一周。第二天我一進教室,看到桌椅就昏倒,從此我就得了自閉症。每天我把自己關在房裡,除了爸爸媽媽誰也不見。”
三毛開始曠課,逃學到墳墓堆裡去讀閑書。不久,就休學了,再也不願意去上學,說不去就不去了。

▲小時候的三毛有點固執和敏感。
她對一切循規守律的事都覺得很累,一個學期這樣上課,對她來說太累了,整天坐着又覺得無聊,自己在家看書反而看得更多,所以自己決定不去讀。
幸好三毛的父母都是通情達理而慈悲的家長。
他們沒有責怪三毛,隻願她沒有受傷太深,惟願她踏踏實實地活着。
他們試着讓她重新打開内心的枷鎖,送她去學插花,學鋼琴,學國畫,跟名家黃君璧習山水,跟邵幼軒習花鳥。
她喜歡看書,她的父親陳嗣慶便教她背唐詩宋詞,看《古文觀止》,讀英文。
直到16歲時,偶然遇上了年輕的畫家顧福生,三毛的眼睛裡才重新有了亮光。
那天,這個孤獨的失學少女提着畫箱,走進了深宅大院,穿過杜鵑花小徑,見到了比她年長不了多少的顧福生。這位青澀的藝術家,是國民黨高級将領顧祝同的兒子。他個子不高,有一張青春俊秀的臉孔,作畫的時候異常專心利落。
作為将門之後卻選擇了藝術之途的顧福生,對三毛不上學這件事,表現得十分自然,也不去追問。

▲少年三毛。
他與三毛的相處,說話總是商量式的,口吻也很尊重。遇到她畫不出來的時候,就要她停一停,還讓她看他的油畫作品。盡管三毛大多是在模仿着顧福生的畫,顧福生也并不在意,隻說:“可以,再畫。”
碰到這樣的老師,天生有一點任性有一點狂的三毛,第一次折服了。
她在自己模仿顧福生的繪畫習作上簽下了Echo(回聲)——這是她給自己取的第一個名字。
顧福生看出了三毛的才華不在繪畫,鼓勵她走出去交朋友,建議她寫作,并向白先勇推薦了她的稿件。于是,她的作品《惑》刊登在《現代文學》雜志上,署名陳平。
一個封閉了四年的孩子,憑着這一點肯定,終于逐漸從那個幽閉的世界小心翼翼地邁了出來。

▲三毛與父母陳嗣慶和缪進蘭。
02短短十個月後,顧福生去了巴黎——那個年代的畫家眼中的藝術殿堂。而三毛此後又輾轉跟了幾位畫家學畫。
直到20歲時,一個亦師亦友的朋友勸她:“你不要一直關下去嘛!這條路這樣走下去不是個辦法。你總得走出來。”
1964年,獲得台北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特許,三毛在該校哲學系當選讀生。
三毛開始更加舍命去讀書,勤勞地去做家教,認真地寫她的《雨季不再來》,也開始轟轟烈烈地去戀愛。這一切大概是她常年休學之後的起跑。

▲年輕時的三毛。
她注意到了隔壁戲劇系的一個男生,比她高一級,才讀大學不久,已經出了兩本書,是學院大名鼎鼎的才子。
出于好奇,三毛特地去借了他的書來看,看完之後大為震驚——他怎麼會寫的那麼好!
這個叫舒凡(本名梁光明)的男孩,一下子闖進了三毛的心。
她開始“如同耶稣的門徒跟從耶稣一樣,他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他有課,我跟在教室後面旁聽;他進小面館吃面條,我也進去坐在後面。這樣跟了三四個月,其實兩個人都已經面熟了,可是他始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我的心第一次受到愛情的煎熬”。(三毛《我的初戀》)
單相思的三毛隻好懷着小鹿亂跳的心,鼓起勇氣主動出擊,一切就像她後來填詞的歌曲《七點鐘》裡寫的那樣:
今生就是那麼地開始的
走過操場的青草地 走到你的面前
不能說一句話
拿起鋼筆 在你的掌心寫下七個數字
點一個頭 然後 狂奔而去
守住電話 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
鈴聲響的時候
自己的聲音 那麼急迫
是我是我是我
是我是我是我
七點鐘 你說七點鐘
好好好 我一定早點到
就這樣,三毛沒有一點少女的羞澀就答應了,赴了今生第一次約會。
約會就在開往淡水的夜車上,那是一場旅程的開始,而她一直沒有下過火車。那列火車叫做“愛情”。

▲三毛的眼裡滿含笑意。
愛情千千種,初戀第一種。兩年後,兩人鬧分手。
三毛想要人家許諾一個未來,可是男生始終不說話。三毛求了又求,哭了又哭,為了逼他,甚至一步步辦理出國手續,結果男生開口了,隻低頭說了一句“祝你旅途愉快”。
最後三毛就真的遠走他鄉了。
從此,開始了一生的流浪。
流浪的第一站是西班牙。在那片異域土地,三毛認識了一個被她叫作“荷西”的西班牙男生。
當時三毛在馬德裡大學讀二年級,而荷西念高三。
兩人一開始隻是很普通的朋友,他們一起踢足球,騎摩托車,打棒球,到舊貨攤購物。每個星期荷西都會到宿舍旁的大樹下等三毛,修女們一看到荷西,就會調侃三毛:“Echo! Echo! 你的表弟又來了!”

▲三毛與她的外國朋友們。
有一天,兩人在一個公園裡閑坐,荷西對三毛說:“Echo,你等六年,我有四年大學要念,還有兩年兵役要服,六年一過,我要娶你。”
荷西告訴三毛,他的願望是擁有一棟小小的公寓,他外出賺錢,三毛在家煮飯給他吃。這種樸實的理想讓三毛感動了,她初戀時所想要的承諾也不過是這樣。
隻是,六年時間太長了,長到足以改變很多東西。
最終三毛選擇了分開,她不允許荷西再到學校去找她,荷西同意了。
在那個公園裡,荷西手裡拿着他從未戴過的法國帽,一面小跑着倒退,一面不住地朝三毛揮手喊道:“Echo! 再見!Echo! 再見!”明明眼淚都快掉下來了,他還扮着鬼臉。
當然,強忍着眼淚的還有三毛,她後來回憶說,“他是一個很難得而且與我真誠、真心相愛的人。我幾乎忍不住要狂喊他的名字,叫他回來。”

▲三毛與荷西。
三毛離開了荷西,又離開了西班牙。
三年裡,她去了德國,在那裡做導遊、做德文教師,卻又匆匆離開,漂泊去了美國。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1970年,她回到了台灣。
她就像一隻沒有腳的小鳥,隻能不停地飛呀飛,身邊的追求者來來往往,而她卻始終沒有找到屬于自己的歸宿,也沒有找到象征自由的遠方。
遠方有多遠請你請你告訴我
到天涯到海角算不算遠
問一問你的心隻要它答應
沒有地方是到不了的那麼遠
三毛又回到了曾經就讀的文化學院,不過這一次是作為一個教師的身份,她教授德文與哲學。

▲三毛。
漂泊過的人,行為應該有些長進,她也一直期待着有質感的穩定感情。
但終究還是不夠幸運。
這邊剛結識了明星咖啡屋的一個畫家,在即将舉行婚禮前,卻猛地發現信誓旦旦說愛她的這個男人早有了妻子;那邊好不容易遇上了一個穩重持成的德國教師,結婚前夜卻因心髒病突發猝死……
愛情的屢次受挫,讓三毛感受到了上蒼的惡意,她一度自殺尋死。
人的一生中,總有些沒辦法得到的東西,一直存在着遺憾。于是她又動起了流浪的念頭,再次離家遠走,又去了西班牙——那個最初的流浪起點。
每個人心裡一畝一畝田
每個人心裡一個一個夢
一顆呀一顆種子
是我心裡的一畝田
用它來種什麼
用它來種什麼
種桃種李種春風

▲三毛。
03在西班牙,她重逢了那個叫“荷西”的大男孩。
三毛沒有想到,他真的如約等了她六年,現在已經長成了留着大胡子的成年男子。他們曾經凝滞了的故事又重新流動了。
其實,三毛第一次遇到荷西的時候,也沒想過要共度一生,但再去的時候,她已曆盡滄桑,或許覺得單純也是一種美麗。
荷西是個興趣十分廣泛的人,他在學校學的是工程,可他愛上了潛水。在這個世界上,他最執着于兩件事:一是從少年時期開始的對三毛的愛,二是對大海的迷戀。

▲三毛與荷西在遊船甲闆上。
和三毛在一起的時光裡,荷西常常會興奮地向三毛講述他在海底的所見,講他同章魚的嬉戲,潛水時的奇遇。
因此,三毛發現,荷西跟她從前的那些男朋友們都不大相同。
從前他們大多愛談論哲學、文學、藝術、人生等大道理,這固然使三毛感到高雅脫俗、深沉智慧,時間長了卻也覺得寬泛乏味。而荷西呢,她幾乎無法和他談論這一類的話題,但又多了意想不到的收獲。

▲三毛與荷西。
有一天,兩人在公園裡散步,三毛告訴荷西明天不能跟他出來散步了。因為她有一篇稿子第二天要交,編輯來信催稿催得緊,然而她卻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寫稿壓力使她焦慮,所以她決定一夜不睡覺都要把稿子趕出來才行!
荷西看她愁苦着臉,就指着公園裡正忙碌修剪樹枝的園丁給她看:“我甯願像這些園丁呼吸大自然新鮮的空氣,在太陽底下幹活,也不願被關在四四方方、密不透風、不見天日的辦公室裡,每天和枯燥的數字、文件打交道,那真讓人煩透了。”
荷西的話觸動了三毛,後來她回到宿舍就給編輯寫信,取消了稿約。
三毛與荷西在一起後,她對生活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變。

▲三毛在荷西西班牙的家中。
也就在這個時候,她想起了曾經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看到過的撒哈拉沙漠的報道,火紅的太陽照着無垠的漠漠黃沙,有種奇異的魅力,長久以來牽動着她的心神。
隻是這一次的沙漠闖蕩,三毛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她身邊多了一位堅定的支持者。
某天,三毛收到荷西從沙漠裡寄來的一封信。荷西告訴她,他已在沙漠裡的一家磷礦公司申請到一個職位,有了工作,等三毛到沙漠時,他會安排好一切來照顧她。

▲三毛與荷西在沙漠中。
荷西為了她,竟放棄最愛的航海,率先跑到了沙漠去。
三毛寫信苦勸荷西,勸他不要為她到沙漠受苦,況且她去了,大半時間也在各處旅行,不能常常見到他。
荷西回信說:“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邊,隻有跟你結婚,要不然我的心永遠不能減去這份痛楚的感覺。我們夏天在沙漠結婚好嗎?我在沙漠等着你。”

▲三毛與荷西在沙漠中公證結婚。
1973年,西屬撒哈拉沙漠阿雍小鎮上,年輕的法官證婚時拿紙的手有點顫抖。
這是沙漠中第一次有人來公證結婚,法官面對着眼前這對異國夫婦有一點小緊張。
荷西曾問三毛:“你想要一個賺多少錢的丈夫?”
“看不順眼的話,千萬富翁也不嫁,如果中意,億萬富翁也嫁。”
“說來說去,你還是喜歡錢。”
三毛俏皮地說:“但是也有例外呀!”
荷西擡起眼:“那如果是跟我呢?”
“那隻要吃得飽就夠啦!”
“三毛,你吃得多嗎?”
“不多不多,以後還可以少吃點。”

▲三毛與荷西在沙漠簡陋的家中。
在蒼涼的沙漠裡,三毛迎來了屬于他們的第一個家——盡管如此狹小、簡陋、破敗,要啥沒啥,水電發愁,簡直都不能稱作能住人的房子。
“這是一種很平淡深遠的結合,我從來沒有熱烈的愛過他,但是我一樣覺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在一種強烈的人與自然對比中,她感受到了心靈的安詳,“隻有在深入大漠裡,看日出日落時一群群飛奔野羚羊的美景時,我的心才忘記現實的枯燥和艱苦”。

▲三毛與沙漠中生活的少年和駱駝。
在那裡,遠離現代文明的三毛重新提起了筆,自願而愉快地記錄着沙漠生活的點點滴滴。
她寫這個被漫天風沙包裹的小鎮,寫她孤獨而忙亂的家庭主婦生活,寫她為荷西做的中國菜,寫她特地觀看沙漠婦女洗澡的奇聞異事,寫她和荷西陷在沙漠沼澤中九死一生的荒山之夜,寫“沙哈拉威人”的婚姻嫁娶、婦女命運,寫風土人情、兒女私情,也寫民族的沖突無奈與人性的貪婪險惡。

▲三毛與沙漠中的少年。
而地球的另一端,也正因為三毛記錄的故事,使得撒哈拉沙漠不再遙遠。
人們第一次将撒哈拉的名字與這個女人連結在一起,并成了一種時代的象征。
三毛生命中最安穩的時光,是和荷西一起度過的,荷西給了她最好的愛情,也給了她最大的自由。
他們都是長情的人,本已決定就這樣平淡地過完一生。
三毛曾在書裡寫:“鐘敲十二響的時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裡,說:'快許十二個願望。’我心裡重複着十二句同樣的話:'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

▲三毛與荷西。
然而,安定的歸屬卻驟然消失。
六年後一個熱烈的夏天,荷西在一次海中潛水時意外喪生。那個一生熱愛大海的人,将他的生命獻給了大海,徒留岸邊的女人抱着回憶度過一個又一個不眠夜。
04荷西葬在生前三毛與他常去散步的墓園裡,從那處高崗上眺望,可以望見荷西從前工作的地方,望見古老的小鎮和藍色的大海。
“一直站在那裡想了又想,不知為什麼自己在這種情境裡,不明白為什麼荷西突然不見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兒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誰的墳,千山萬水的來與我們相聚,而這個夢是在一條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結束。”(三毛《背影》)
三毛曾對她的大姐陳田心說:“姐姐,我活一世比你活十世還多。”
陳家大姐也曾接受訪談說自家妹妹,活得太真實,愛得太用力,因而一生都過得很辛苦。

▲三毛在書房。
荷西去世後,三毛回到了台灣,同年出發奔往中南美洲,遊走了十多個國家,半年後回來寫下《萬水千山走遍》。
她踏遍青鳥不到的地方,看過部落裡奇怪的自殺神崇拜,又在草原烈馬上回憶往事,想念荷西。
“到底跟荷西是永遠的聚了,還是永遠的散了,自己還是迷糊,還是一問便淚出,這兩個字的真真假假自己就頭一個沒弄清楚過,又跟人家去亂說什麼呢?”(三毛《夢裡花落知多少》)
出走歸來,三毛陸續接受邀請在台灣環島演講,聲名更噪。

▲三毛。
那個時代,男生讀金庸武俠希望行俠仗義,女生讀三毛遊記渴望活出浪漫人生。
這個穿波西米亞大花裙的女人,大眼睛和黑發中藏着屬于吉普賽女郎才有的喜樂和奔放,她的流浪意識和不加掩飾的個性,如同一杯陳年醇酒,越品越上頭。
1990年,三毛寫下她的第一部電影劇本《滾滾紅塵》,這也是她最後一部作品。
電影上映後取得空前的成功,一舉拿下了第27屆台灣電影金馬獎八項大獎,獨獨三毛一人入圍了編劇獎,卻未獲獎。

▲三毛與《滾滾紅塵》主要演員合影。
電影的主角是沈韶華和章能才,演員是林青霞和秦漢,講的是張愛玲(點我)與胡蘭成的故事,而三毛心裡想的卻是自己與荷西。
一部電影道盡了三個傳奇女子的愛情沉浮,然而滾滾紅塵中,戲裡戲外竟沒有一對善終。
1991年1月4日,三毛用尼龍絲襪上吊自殺,卒年48歲。
這個終生都在追求自由的女子,自殺前告訴友人說她是“不自由”的。
她曾說自己的人生異常的豐富,惟她辭世,卻未留隻字片語,徒留世人臆測。

▲三毛在成都。
三毛自殺後的第二天,台北氣溫降了很多,天氣奇冷。
三毛的母親缪進蘭穿上三毛從大陸為她帶回來的紅毛衣,捧着三毛1月1日提早送她的生日禮物,一尊玉雕和一張卡片,流淚接受親友的慰問。
她說,三毛很少送她生日禮物,嫌俗氣,這一次卻忽然送了生日禮和卡片,她的反應是:“咦,不是下個月才生日嗎?”三毛說:“怕晚了來不及。”
三毛在卡片上寫着:“親愛的姆媽,千言萬語,說不出對你永生永世的感謝。你的兒女是十二萬分尊敬、愛你的。”署名“次女妹妹”。
所有的“愛”字都畫了心形,童稚而溫馨。
對于愛女的自殺,父親陳嗣慶後來回憶:“我女兒常說,生命不在于長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過。我想這個說法也就是:确實掌握住人生的意義而生活。在這一點上,我雖然心痛她的燃燒,可是同意。”

▲三毛在成都。
三毛寫過一首歌叫《橄榄樹》,歌兒是這樣唱的: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流浪……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澗清流的小溪
為了寬闊的未來
流浪遠方,流浪……
為了我夢中的橄榄樹,橄榄樹……
世間有無數的悲劇,如夢如幻。就像三毛所說:“人如飛鳥,在時空的幻境裡翺翔。”
也許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夠完美,但我們可以确信,她終生都在求真,終生都在對抗虛幻。
參考文獻:
師永剛、陳文芬等編著:《三毛:1943—1991》,作家出版社,2011年
三毛:《三毛作品集》,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
齊豫、潘越雲:《回聲:三毛作品第15号》,滾石唱片公司,1985年
下一篇
工程師思維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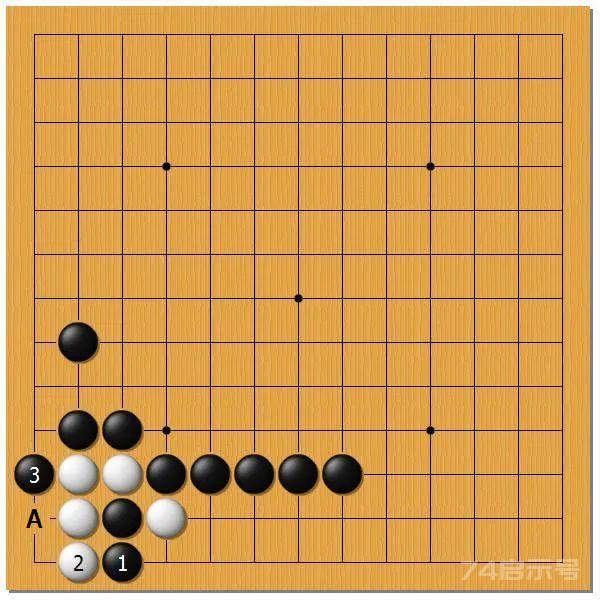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