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名篇賞析《西湖的風》 柯靈
- 旅遊
- 1個月前
- 54
地上的樂園早經失去,人間的天堂都已毀滅……
我們的藝術家常常精通商業三昧;而商人卻總兼有着名士才情。多謝那一片玲珑心機,如今我們閑情的士女,隻要略略破費,在“孤島”上也得從容地欣賞淪陷了的西子風光了。
哦,這一帶木頭的雉堞,俨然是杭州城廓,圍着一片擾攘與太平。靈隐古刹也建立在缭繞的脂粉香中了,雖然缺少些參天的古木,四周未凋的綠樹,在遊客的心裡也該有些涼意?這裡是紫霞洞,過去點兒還有飛來峰,人工的堆砌也居然不缺乏丘壑之勝;小溝裡一樣浮着遊艇,且有着比湖上更加美豔的船娘。“三潭印月賞中秋”,難得是團圓佳節,先别管世亂年衰,萬人失所,我們也得有一夜狂歡。你看這電炬下的長堤蜿蜒,樓台隐約,這一池子的水還不夠我們幻想的遊泳嗎?……
偉大的匠心!先生,你們真使我不能咽下這一聲贊歎了。
可是,我這不懂風雅的俗人,卻無端的引起了憂煩。你自然不會知道,我的家正在浙東,離錢塘江還不到百裡,離鄉和還鄉那是道必經的津梁。在義渡的木船上望着連天煙水,我曾多少次因為出遊和還鄉的喜悅,在心裡親切地叫着它的名字,像叫着久别的親友。去年秋天,錢塘江上架起了鋼鐵大橋,——那是個稀有的大工程,國家為它耗費過巨量的物力,無數人為它流汗,千餘個工友因為工作被夜潮卷去。——火車可以從上海一直通到我們故鄉了。……可是誰知道現在成了什麼樣子?橋呢,毀了,當然。我想得出那殘斷的骨架,在嗚咽的江聲中傲然獨對西風。堤岸寂靜,除卻天邊的雲樹,沙灘上的鐵蒺藜,江上失去了白色的帆影,岸畔也不見一個行人。夜來了,濤聲拍岸。子夜的潮頭狂怒地湧起,迎着下弦的月色,唱出它滿腔悲憤。
自然你更不知道,杭州城裡有着不少我的故舊和新知,湖上也曾有我繁密的屐痕,如今我還摸得出那一把歡喜與哀愁。杭州的街道在喧擾中也有着平靜,一道柳蔭掩映,隻能給少婦在岸邊搗衣的浣紗溪,象征着的正是杭州的情調。西湖是杭州人的驕傲,那一湖的煙波,一堤的細柳,一帶的層巒,詩人為它們傾倒,闊客為它們一時間也起了閑逸的心。而杭州人是吃了麥稀飯也要餓着肚子遊西湖的。這些平靜慣了的人,平常我讨厭他們,這一會卻有了衷心的懷念。美色對于女人,在亂世隻是一面招攬暴客的酒簾,秀麗的湖山勝迹,在炮火下更不堪聞問,西湖的劫數,誰又能夠想像呢?前夜有客自湖畔來,問起消息,他隻有搖頭與歎惋,眼睛泫然了,可是射出來的是憤怒和複仇的光。他說一切傷心都無從說起。
聰明的先生,我真佩服你們的機智。可是人的思想是奇怪的,你看,我的思路這一下子被引得多麼遼遠?湖山如夢……說真的,一切到過杭州的人,他記憶裡的湖山比你們創造的世界更闊更美。而現在西湖的風裡是夾着血腥氣的,我們聞得出。湖畔的一根草一朵花,我們也應當看得出那含愁的顔色。
告訴我,先生,我們幾時能夠到真的西湖,去看看那無邊的煙水,或者,你可以告訴我們一點湖畔的真的消息嗎?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
寫杭州西湖,該是優美抒情的文字。然而我們卻讀到了這樣悲憤慘烈的開頭:“地上的樂園已經失去,人間的天堂都已毀滅……”
看一下文章後面的寫作日期:1938年10月18日,我們便不會覺得奇怪。這時,日寇的鐵蹄正在踐踏祖國的大好河山,國土淪喪,國難當頭,無數中國人流離失所,慘遭蹂躏。西湖杭州,也已淪陷多時。作家在那時發出如此悲怆的呼喊,就不奇怪了。
那一年,上海的一家電影公司搞了一個“西湖博覽會”,用布景搭出西湖風景,讓“孤島”上的士女遊覽,很多善男信女還去那假的靈隐寺進香,在上海灘引起了轟動。柯靈的這篇散文就緣發于此。
辦“西湖博覽會”的動機,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以此激發人們的抗日之心,現在已經無法确定,也許兩者兼顧。但對于故鄉就在離杭州不遠的柯靈來說,這樣的博覽會隻能引發他的一片憂國懷鄉之情。文章的前兩段,有很濃的諷刺意味。柯靈用“商業三昧”、“名士才情”、“玲珑心機”這樣的詞彙來形容“西湖博覽會”的主辦者,譏貶之意非常明顯。而對博覽會的描繪,看似贊美,實為嘲諷。景棚裡的西湖勝景,盡管獨具匠心,卻總是虛假,也難改國土淪陷的現實。“難得是團圓佳節,先别管世亂年衰,萬人失所,我們也得有一夜狂歡”,這樣的抒情,當然是反話正說,内中蘊涵的慘痛,當時的讀者人人都能讀出來。
然而柯靈寫此文決不僅僅是為了諷刺,這個粉飾太平的博覽會,在他的心裡“無端地引起了憂煩”。這“憂煩”是什麼?是亡國失友之痛,這才是文章的主旨。此文的中間兩大段,柯靈滿懷深情地寫了對故鄉和西湖的懷念,在他的回憶中,“那一湖的煙波,一堤的細柳,一帶的層巒”,是天下最美麗的景象。他懷念故鄉的山水,也想念故鄉的人民,想念杭州城裡的故舊和新知,對平時他所讨厭的“平靜慣了的人”,“這一會兒卻有了衷心的懷念”。他想像着淪陷後故鄉的滿目瘡痍,想像着人們在鐵蹄下遭受的苦難,心情沉重。
文章結束時,柯靈又把諷刺的筆墨贈給那些具有“偉大的匠心”的“聰明的先生”,他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一切到過杭州的人,他記憶裡的湖山比你們創造的世界更闊更美。而現在西湖的風裡是夾着血腥氣的,我們聞得出。湖畔的一根草一朵花,我們也應當看得出那含愁的顔色。”
文章用诘問收尾:“告訴我,先生,我們幾時能夠到真的西湖,去看看那無邊的煙水,或者,你可以告訴我們一點湖畔的真的消息嗎?”這是發自心底的期盼,其中似乎也有提醒那些醉生夢死的雅士們的意思,提醒他們不要忘記嚴峻的現實,不要忘記抗日救亡、收複國土。面對這樣的诘問,讀者能不為作者那摯切深沉的愛國懷鄉之情所動?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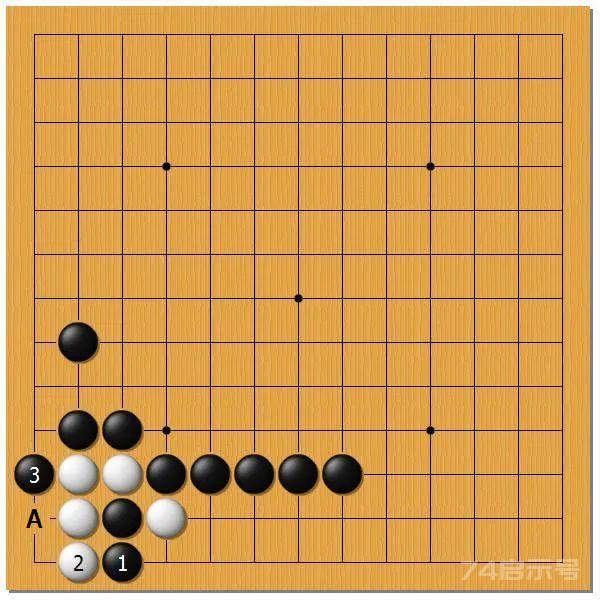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