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儒與法的“愛恨情仇”
- 綜合
- 2年前
- 172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趙慕宇
二十世紀以降,深受西方沖擊的中國學界,始終面臨“何以自處”的問題——西方的崛起,無疑映襯着落後的東方帝國。然而,西方在近代的領先,一定意味着東方的衰落嗎?抑或是中華帝國自身制度導緻的周期性毀滅?
著名社會學家趙鼎新教授的《儒法國家:中國曆史新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套新穎而完整的闡釋邏輯。他以“儒法國家”的概念統攝中國曆史,意在說明自漢代以來,儒法體制為中央集權帝制帶來很強的彈性與韌性,使其能夠與儒家精英階層合作,改良而非推翻政治格局;同時,促成政治與意識形态統一,轄制并利用軍事力量。
在深入理解儒法體制前,有必要理解本書所使用的理論體系。首先,曆史是積累性構造,競争所産生的制度化,是曆史變遷的主要動力;其次,本書運用邁克爾曼的四項權力——即經濟、軍事、政治、意識形态為基本框架,分析其互動關系,及其對曆史造成的影響。

《儒法國家:中國曆史新論》趙鼎新 浙江大學出版社
封建危機:擴張與貴族
西周時期,分封制和宗法制維持周王室的統治。周代最初為防禦而建立大小不一的據點,随後其中強大者吞并弱小者;強大國家接着發展為多城邑國家,國君所居為“都”,小宗管轄城市為“邑”;到東周時期,多城邑國家憑借實力控制更多領土,最終轉變為領土性國家,這便是“五霸七強”的形成軌迹。
整個東周時期,最重要的變化是西周封建制瓦解。趙鼎新認為,東周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霸主時期(前770—前546),這一時期諸侯野心膨脹,擴充領土的目的是成為能夠支配其他國家的霸主,除楚國外,所有國家都扮演着周王室保護者的角色。霸主體系下,國君勢必依靠更多官僚進行管理,作為國家官員的世卿貴族擁有領地和武裝,最終,大宗巨室勢力越來越強勁,使原有體制瓦解。
轉型時期(前545—前420)始于封建危機的深化,終于官僚制領土國家的出現。沒有霸主遏制後,小國貴族公然擴充自己勢力,以擠壓國君的權威。在這一時期,土地私有制、官吏選拔、軍事組織、商業活動等,都在發生變化。最終以法家改革為标志,進入全面戰争時代(前419—前221)。
全面戰争時代,幾乎完全擺脫封建制限制,諸侯國通過改革,創建“全權國家”,使國家最大限度增加财政稅收和軍事力量。此時戰争主要是追求經濟利益和攫取政治霸權,其核心目的是擴張領土和削弱敵人,因此,戰争變得極為殘酷,幾乎大部分男性人口都會被動員。
不難發現,由春秋到戰國,實際上是封建制崩潰的過程,而促成這一變化的是國家的擴張以及貴族世家的膨脹。根據本書統計,貴族勢力的增強與該國政權的繼承危機呈正相關關系,魯、齊、晉這樣封建危機最劇烈的國家中,有半數國君于在位期間被殺。
世卿貴族的強大,主要是由于軍事擴張後,新拓展疆土需要有效管理。因此國家版圖越大,封建貴族的勢力就越大。比如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事件,既是春秋、戰國的分界,也是貴族争權的著名事例。楚國大夫申無宇所總結的“尾大不掉”,可謂是對貴族膨脹的精準描述。
封建危機中的貴族地位變化使官僚制和郡縣制也得以發展。國君把擴張的領土新派給制定官員來管理,“縣”作為行政與軍事單元出現。一縣之長的全面負責,為之後的帝國政治結構奠定了基礎。
秦國之興:法家的凱旋
各諸侯國因封建制的瓦解,使貴族掌權成為常态。然而,處于邊陲的秦國,卻因為“落後”,政治結構相對簡單,貴族階層勢力有限,易于形成“強國家、弱貴族”的格局。正是這一點使其在全民戰争中脫穎而出。
秦國沒有“傳統”的包袱,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法家改革。商鞅變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個能緊密控制臣民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打造一個可組織、可延伸的軍隊,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赢得戰争勝利。
相比于“集約型技術”,即更少勞動投入換取更多産出,法家所采取的是“粗放型技術”,即通過更廣泛、更嚴密的勞動力資源獲取産出,這種模式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國家。針對魏特夫“水利工程促成集權制度”的觀點,趙鼎新認為,水利工程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正是由于強大的組織性,“強國家”傳統的諸侯,才能修築為戰争和生産而準備的水利工程。

秦始皇陵銅車馬展示秦國威勢
此外,法家所打造的國家,具有“重農抑商”色彩。法家認為,商業繁榮會導緻國家軍事力量的衰弱,農業生産更有助于國家在戰争中赢得勝利,而農業所創造的定居人口,為國家提供了穩定兵源。在秦始皇上位的過程中,商人呂不韋至關重要,最終卻被清剿勢力。這一事例也是法家治國下,商人難以逃脫的宿命——“商人通過走進國家體制内部來獲取權力,這就導緻國家建構與商人群體之間出現了零和博弈的局面。”實際上,在古代皇權社會,這一矛盾始終存在。
簡言之,法家将秦國打造成一部高效率的戰争“機器”,這一點也被認為是“秦王掃六合”的重要原因。但是,僅關注成功者的經驗是偏頗的,其他六國何以失敗,也需着重對比研究。
其實,最早進行法家改革的不是秦國而是魏國,魏國處于四戰之地,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種處境也逼迫魏國最早破局,開啟戰國時代的攻伐。而魏國失敗的原因,主要是不利的地緣政治條件以及沒能維持與韓、趙的聯盟。
趙國與魏國有着相同的困境,趙國與他國接壤土地極多,還必須面臨北方匈奴日益高漲的威脅。其次,趙國農業産量遠不及秦國,最顯著的例子是長平之戰中廉頗堅守戰術的“破産”,一部分原因就是糧草難以支撐趙國在上黨前線的消耗。
齊國作為貴族傳統悠久的國家,始終難以像秦國一樣徹底改革,其政治體制具有極強的折中性。齊國甚至在法家工具理性、儒家道德、道家自然中達成某種平衡。齊國雖有地利,最終卻沒有轉化為軍事優勢。
楚國的貴族與王室也在維持一種相對平衡狀态,而這種政治平衡逐漸演變為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成為保守主義的根源。楚國是各大國中唯一允許貴族具有大量私人武裝的國家。
此外,戰國時期的國家關系,也處于霍布斯式的混亂狀态,六國之間彼此猜忌、互相算計,生怕某一國獨大,為蠅頭小利而相互攻伐,最終也難以形成合力。
秦國在封建瓦解中的“後知後覺”,恰恰減輕了貴族政治的影響,從而最大程度打造出君主制集權,法家思想及其改革,獲得了最終勝利。
儒法調和:穩定的結構
秦國統一天下,看似無比強大,但全面戰争時代沿襲下來的政治體制,帶有很強的不穩定性。秦朝對自己發展出來的高效能組織及嚴苛手段過于自信,因此也不屑于與社會精英合作。諷刺的是,導緻秦國崩潰的原因恰是社會管控能力強所導緻的苛政——秦始皇在當時能夠征發全國15%的人口為其修築工程。這一調動即便是現代國家,也要頗費周章。
漢高祖奪取天下後,漢初政治進行了兩項變更,一是用黃老之術恢複民生,二是郡縣制與分封制并行。漢高祖之所以建立同姓封國,原因在于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優勢還沒有得到“短命”秦朝的充分印證,另一方面緣于分封制也是防範、限制呂後等外戚勢力的手段。
顯然,随着後來“七國之亂”的爆發和平複,政治軌迹再一次回歸到中央集權制。彼時漢朝面臨三個重大問題:其一,人口生産恢複後,商人和地主利益膨脹,造成土地兼并;其二,随着削藩推進,官僚選拔沒有穩固的體系;其三,黃老之術和法家,都不能為國家提供一套支撐其合法性的意識形态,無法為政權和精英群體提供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此背景下,董仲舒發展出的理論,被統治者所重視。他提出長幼有序、尊卑有别,君主處于權力頂端,法律刑罰維持社會秩序的觀念。這無疑是一種綜合性意識形态,也便是所謂“帝制儒學”。

董仲舒
“帝制儒學”不僅為儒家思想延續“壽命”,更重要的是易于被精英階層接受,它鑄就了君主與臣屬的共生關系,是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态權力真正結合。由此,皇帝接受儒家的教育,官僚體系既受到君主的絕對支配,也憑借“道統”獲得批評權力。有漢一代,注重道德的選官方式,正是這種意識形态的延伸。
老子言“反者道之動”,不難發現,正是由于法家的嚴苛性質,漢朝統治者進行了儒家的調和。自此之後,“儒法國家”體制形成,并一直延續至近代。儒家之所以能夠後來者居上,是因為它提供了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維護了道德秩序,不斷強化穩固的社會制度,為國家選取官僚,同時又使君主有力掌控着官僚系統。
實際上,儒法體制并非沒有受到過挑戰。比如南北朝到隋的分裂時期,正是由于軍事權力失控,導緻攻讦頻發。強大的軍權獲取政權,卻又擔心另一個軍閥取而代之,政權與世家大族若即若離的不穩定關系,最終難以形成官僚體系。唐代初期的科舉制和府兵制,對于穩定政權起到極大作用,背後原理也是恢複到儒法國家的結構——軍事權力得到轄制,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态結合,重新占據主導權。
儒法國家的概念,最終也引領我們反思近代的變革。在趙鼎新看來,西方的崛起恰是因其競争和沖突未能被有效制度化,資産階級擁有更多自主權,引發新秩序的建立。而中國封建曆史上體制的循環,仿佛是一種“螺旋式”的自我重複,即便沒有十九世紀的西方沖擊,清朝也依然會爆發矛盾。
本書對儒法國家形成過程具體而微的分析,十分精彩,同時能夠利用社會學、政治學的框架與概念,進行結合式研究,讀罷令人豁然開朗。也許,正如本書所堅信的那樣,曆史的積累性和斷續性,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看似堅固無比的事物,都有其難以察覺的發端以及煙消雲散的終結。(責編:張玉瑤)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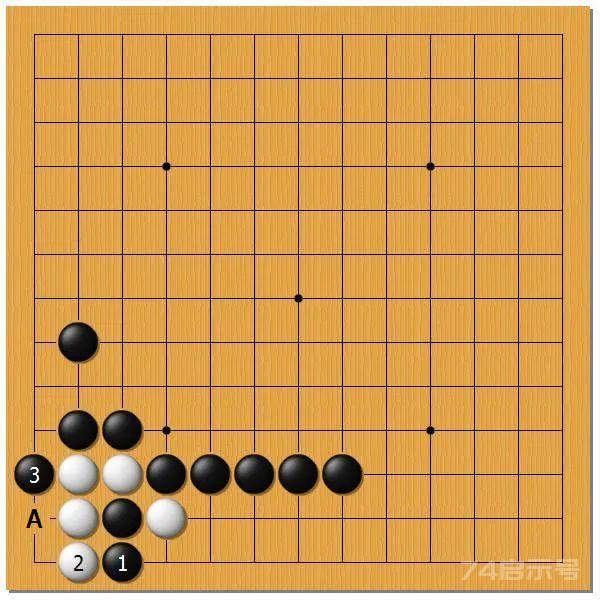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