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洪永|你再好,也有人讨厭
- 财經
- 2年前
- 214

金無赤足,人無完人,
再美的人,也有不足,
再好的人,也有缺點!

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都是單一的個體,
我們都有一身的毛病,
不管做什麼,都有人看不慣,
不管說什麼,都有人不喜歡!

人和人不一樣,
有的人看到美好,
有的人記住煩惱,
有的人喜歡安靜,
有的人喜歡熱鬧。

不一樣的人,
就有不一樣的想法和看法。
你再優秀,也有人指點,
你再普通,也有人喜愛。
别人眼中的你,
不是真實的你,
他們看到的隻是表面,
真正的你隻有你自己了解。

不要為了流言蜚語生氣,
不要因為指點議論傷心,
你隻要做好自己,
人品端正,心地善良,
坦坦蕩蕩,本本分分,
就不會在乎别人的議論。

我們不是鈔票,
做不到人人追捧,
我們不是黃金,
不能讓所有人愛惜。
我們隻是普普通通的人,
有缺點和毛病,
有優點和長處。
喜歡你的人,就不會在乎你的不足,
讨厭你的人,更不會發現你的好處!
據《尚書•呂刑》記載,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時說:“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鸱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這段話的意思是:蚩尤一開始作亂就禍害到了百姓,他的種種行為不僅沒有對那些貪婪得像鹞鷹一樣的人的嚣張氣焰構成預防和打擊的效果,反而使他們裝出一番虔誠的奉上峰命令架勢,更加瘋狂的去掠奪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聽從蚩尤的命令。在這種情形下,蚩尤制定種種嚴酷的刑罰來威逼九黎族人服從,并美其名曰“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壞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種嚴酷的刑罰就開始濫加施行并成為制度了。從此以後,那些貪婪之徒殺人掠奪都有了華美的托詞,他們說他們這樣做是依法行事。這樣,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亂哄哄的幹起壞事來。這一段記載給了後世讀者一個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時期倡令作亂的兇頑之徒。如果你有興趣再讀一讀其它史籍的話,或者如果你有興趣還去讀一讀像《龍魚河圖》、《遁山開甲》等五行、谶緯或者志怪類如《述異記》等古代典籍的話,你會發現蚩尤的形象幾乎被定格了:暴君、亂賊、貪婪兇頑之徒,一句話,這是一個絕對的反面形象。也許與“暴君、亂賊、貪婪兇頑”有關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麼怪異:“銅頭鐵額”、“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僅如此,就連“蚩尤”這個名号也是怪怪的:《廣雅釋诂》:“蚩,亂也。”《方言》:“蚩,悖也。”又說尤,同由尤,是人肚子裡一種蟲;“蚩”、“尤”合起來意思就是一種行為悖亂的蟲子,這自然是人們一句字義望“字”生義的結果。如果說《龍魚河圖》、《遁山開甲》、《述異記》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異而有意塑造蚩尤這樣的怪異形象的話,人們望字生義而诠釋蚩尤名号的意義則有明顯的歧視、貶損、嘲諷等負面意義。那麼,人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裡要說一段重複的話。我在《從史籍中看炎帝和黃帝》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司馬遷采信《大戴禮記•五帝德》、《大戴禮記•帝系》的記載和觀點,以黃帝為五帝之首,實際上就是以黃帝為尊,也就是以黃帝為正統,自然,舉凡與黃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統的,也就是非正義的了。用春秋筆法來記載和叙述非正統、非正義人物的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對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動斥之為‘侵淩’了。”《大戴禮•用兵》把蚩尤說成是“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劂親,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無厭者也。”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由此推而廣之,蚩尤與黃帝有過敵對行為,而且,很有可能,終蚩尤一生,他與黃帝隻有敵對,沒有合作。所以,人們在評述蚩尤的種種行為及由此而來的功過是非時,也受這種意見支配,并且,較之于評述黃帝的其他曾經有過敵對關系的對象,其批評、貶斥的主觀态度又更為顯著。司馬遷是這樣,其他古代史學家也是這樣。
《史記•五帝本紀》說:“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逐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這一段話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亂賊、貪婪兇頑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證了《尚書•呂刑》的記載。但是,它給人留下的懸念實在太多了。
《史記•五帝本紀》在記載黃帝為建立統一的國家雛形所進行的一系列戰伐活動,重點記叙三場戰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戰,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戰,安定北方的北逐葷粥之戰。人們不禁要問:司司馬遷為什們要單單叙述這三場戰争呢?
阪泉之戰促成了黃帝、炎帝氏族部落聯盟的産生,奠定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雛形的基礎,為人類社會迎來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義深遠,值得一記;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劍指北方少數民族,發動北逐葷粥的戰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時,彰顯了新興氏族部落聯盟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綜合實力及影響,在堅決打擊敵對勢力之餘,震懾了其它潛在的敵對和分離勢力,其政治意義勝過軍事意義,是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共同維護和鞏固統一民族和國家雛形而進行的一場宣傳戰,意義非凡,也值得一記。那麼,涿鹿之戰為什麼也值得一記呢?我們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來搜尋有關線索:
《山海經•大荒北經》說:“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殺蚩尤。”《龍魚河圖》說在涿鹿之戰的初期,黃帝“遂不敵”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幫助下才制服蚩尤。《黃帝玄女戰法》說:在涿鹿之戰中,“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最後在仙女的幫助下才戰敗蚩尤。《玄女兵法》則說:“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這裡說“九戰九不勝”、“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戰雙方都比拼神力,或黃帝一方的神靈暗中相助,這才取得勝利,無非是說蚩尤是很強大的對手,其戰鬥力不亞于黃帝,甚至比黃帝還要高強,因此,仗打得慘烈,赢得艱難。這是涿鹿之戰值得一記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書•嘗麥解》有這樣一段記載:“昔天之初,誕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臨四方,司__(缺兩個字)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翼。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辔之野。”這段話的意思是從前,天下還沒有安定的時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黃帝兩個聖人,他們降生之後,才開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這個過程中,黃帝授命炎帝分派兩個官員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讓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東任職。可是,蚩尤卻在那裡興兵作亂,驅逐炎帝,炎帝大敗而逃,蚩尤一路緊追,一直追到涿鹿,并進行了更為激烈的交戰。炎帝非常害怕,隻好先黃帝求援,黃帝就出兵與蚩尤作戰,最後,将蚩尤戰敗,并把戰敗的蚩尤殺死在冀州一個叫“絕辔之野”的地方。
這段記載可以補充司馬遷上述記載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戰發生的原因和大緻經過:蚩尤氏族部落歸屬了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在職務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屬;當炎帝奉命委派兩個官員去管理地方事宜時,炎帝作出了讓蚩尤一同去山東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東一帶,這說明炎帝和蚩尤除職務上的上下級關系之外,可能還有其它特殊的關系,這為蚩尤到山東以後,積蓄力量,整軍備武,最後,舉兵驅除炎帝創造了機會;蚩尤舉兵驅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敗,這說明蚩尤擁有一個強大而又有實力的集體,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則是這個氏族部落的首領;黃帝讓炎帝派蚩尤去山東赴任,也就是讓蚩尤氏族部落遷徙到山東去,對于蚩尤氏族部落來說,這是被迫背井離鄉,這應該是導緻蚩尤舉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戰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蚩尤逐炎帝,後一個階段是炎帝聯合黃帝共同戰勝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聯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亂,屬于平定内亂的戰争。
涿鹿之戰是一場平定内亂的戰争,它的發生時期很特殊,因此,意義非同一般:涿鹿之戰發生在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雛形形成初期,平定這樣的叛亂直接關系到了這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雛形的存亡和發展。這是涿鹿之戰值得一記的主要原因。
《逸周書•嘗麥解》的記載也許是可信的,所以,後世有不少史學家采用了這段記載。其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羅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後紀四》中是這樣轉述的:
“炎帝參盧,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務乘人而鬥其捖,于是諸侯攜貳,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禦,蚩尤産亂,逐帝而居于涿鹿,頓戟一怒,并吞亡親。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之。參盧大懼,設襢于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後,鄧伯溫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辯者賓祭于熊,爰代炎輝,是為黃帝,乃封參盧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陳。”
羅泌的轉述較之《逸周書•嘗麥解》的記載更為詳細。第一,他告訴我們,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領,也就是炎帝,名叫參盧,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來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個地名,大緻在現在的魯西豫東地區。第二,到炎帝榆罔時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處于不穩定狀态,面臨分崩瓦解,這說明此時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經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處在這樣的困境時期,炎帝派蚩尤去鎮守山東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東後,蚩尤接受炎帝的節制,但是,炎帝卻缺乏節制蚩尤的實力,于是,蚩尤乘機起兵驅逐炎帝,這說明,炎帝和蚩尤同屬一個氏族部落,他們之間是一種上下級關系;蚩尤舉兵驅逐炎帝,也就是争奪氏族部落的領導權。第五,在連吃敗場之後,炎帝求助于黃帝,黃帝派鄧伯溫等人領兵戰敗了蚩尤。這說明此時炎帝氏族部落已經歸屬了黃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組成炎黃氏族部落聯盟。第六,戰勝蚩尤對于鞏固和壯大以黃帝為首的氏族部落聯盟有着非凡的意義,黃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羅泌的這一段轉述很容易使人産生這樣的聯想:炎帝為戰勝蚩尤而歸順黃帝并與黃帝組成炎黃氏族部落聯盟,我們能否由此推斷炎帝和黃帝之間是先後合作後又分裂呢?這樣的聯想至少可以引出兩個問題:其一、是涿鹿之戰促成了炎黃兩個氏族部落的聯合嗎?其二、是先有炎帝、黃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戰然後才有炎帝、黃帝之間的阪泉之戰嗎?
這兩個問題的支撐點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不妨用解讀文本的方式來探讨這個問題。在羅泌的轉述中有三處缺主語:“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禦,蚩尤産亂”。從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點來看,這裡應該是承前省略主語,這個省略的主語是“炎帝參盧”。“政束務乘人而鬥其捖,于是諸侯攜貳,乃分正二卿”,這是說炎帝榆罔時期,炎帝氏族部落聯盟領導層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對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這導緻了子氏族部落的離心離德,由此引發了氏族部落聯盟内部的動蕩不安。在這樣的特殊背景條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對氏族部落聯盟的最高領導層進行了調整,确定了自己與蚩尤在氏族部落聯盟内一正一副兩個最高領導職務,與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聯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臨西方、司百工”,這是說在具體分配工作的時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東一帶,這是炎帝氏族部落聯盟的西部邊境。到此為止,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間的争鬥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聯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務,我們不妨稱其為“内讧”。“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之。參盧大懼,設襢于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後,鄧伯溫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這是說作為新興的天下共主,黃帝的實力和影響力正如日中天,不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擁戴,而且,在走投無路的狼狽處境下,作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這就促成了炎黃氏族部落聯合,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共同戰勝了蚩尤。如此說來,問題的答案似乎應該是這樣的:涿鹿之戰促成了炎黃氏族部落的聯合,先有涿鹿之戰,後有阪泉之戰。
父,《說文》的訓解是:“巨也,家長率教者。”這就是說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擁有對人行使統領、管教權力的人,即首領。後來,“父”的這個意義被“後”、“帝”所取代。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我們不妨也用解讀文本的方式來看一看《逸周書•嘗麥解》。“昔天之初,誕作二後”,這“二後”指的是誰?從“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來看,“赤帝”乃是“二後”之一,從“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來看,另一後應該是黃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這裡承前省略了兩個主語,前一個主語是黃帝,後一個主語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黃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兩個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這說明在涿鹿之戰前,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已經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東赴任履職,這說明赤帝和蚩尤之間是一種上下級關系。聯系下面叙述蚩尤舉兵驅逐炎帝的情節來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屬于同一個氏族部落,而且,他們是這個氏族部落的兩個重要首領。所以,蚩尤逐赤帝應該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奪領導權的鬥争。再讀《路史•後紀四》所附的《蚩尤傳》,我們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間鬥争的性質:
“帝榆罔立,諸侯攜,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産亂,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興封禅,号炎帝。”
這一段話意思是:榆罔繼承炎帝地位的時候,氏族部落聯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為政,以強淩弱,氏族部落聯盟面臨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選派兩名得力官員區地方上管理個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東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種工匠。但是,蚩尤的實力和影響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無法駕馭蚩尤,蚩尤乘機興兵作亂。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營空桑,把炎帝榆罔驅趕到涿鹿。之後,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稱炎帝,并舉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儀式。
這一段話說得十分明确:蚩尤驅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領炎帝。
那麼,怎樣來理解《逸周書•嘗麥解》和《路史》對這段史實叙述的不同之處呢?我們認為三者之間可以互為補充,《逸周書•嘗麥解》着重于交代事件發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戰是在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形成之後發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後來了一段這樣的評述:“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作者認為,蚩尤興兵驅逐炎帝,這是“以甲兵釋怒”,用戰争說話,述說自己内心的不滿。聯系前後文來看,蚩尤不滿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給自己的職務和工作。作者又認為,黃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亂這是順天意,有利于穩定炎黃氏族部落聯盟内部的穩定和有序運作,所以說平定蚩尤之亂是“用大正順天思序”。我認為,這樣的評述是緊扣涿鹿之戰繁盛的背景來說的。《路史》的轉述則着眼于“展示細節的真實”,補充說明《逸周書•嘗麥解》叙事細節方面的不足。
《蚩尤傳》的上述叙述給後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呂思勉等前賢經過考證以後認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個地方,阪泉之戰和涿鹿之戰乃是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兩場戰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場戰争中前後兩個階段中的兩場大仗。以此為一個依據,呂思勉等前賢認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個人。我認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在同一個地方進行不同的戰争,在同一個地方進行不同戰争的未必就是同一個人。今人劉俊男老師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論述炎帝不是神農,然後從十一個方面舉證論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贊同炎帝不是神農,但并不是說炎帝和神農之間沒有任何關系。我認為就單純的名稱這個意義來講,神農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後不同時期的首領。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從《逸周書•嘗麥解》和《路史》的叙述來看,蚩尤和炎帝之間應該也有一種特殊關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時期的兩個主要首領。所以,《遁甲開山圖》說:“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後紀四》說:“蚩尤姜姓,炎帝後裔也。”一般認為,榆罔是神農、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領,而蚩尤則與榆罔同時,這與《遁甲開山圖》、《路史》說蚩尤是炎帝的後裔并不矛盾。從《蚩尤傳》來看,蚩尤有過逐炎帝榆罔而自立為炎帝的舉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蚩尤是衆多的炎帝中的一個,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斷定蚩尤就是與黃帝同時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這是不恰當的。
蚩尤與炎帝同屬一個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後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動地、活動範圍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疊實屬正常。當炎帝氏族部落歸順黃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組成炎黃氏族部落聯盟以後,作為炎帝氏族部落的後裔及炎黃氏族部落聯盟的一個中成員,從職業上來說也好,從職務上說也好,蚩尤從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這也是正常的現象。當蚩尤與黃帝交惡的時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傳統以火攻黃帝,與黃帝以譴責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狀去譴責蚩尤,這也屬正常現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嗎?這些都蚩尤與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戰神,蚩尤主法主罰,德合熒惑星,即火星,所以,與火星相對應的炎帝,也體現了蚩尤的特征。但是,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間帝王的臣佐陪人間帝王的祭祀體系之後,我們就會發現,作為神靈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還是有區别的。《淮南子•天文訓》說:“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這段叙述告訴我們: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現為太陽,人間帝王炎帝與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間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說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種說法),與人間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現為熒惑星,熒惑星就是火星。這樣的表述暗合炎帝與蚩尤的關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陽和火星一主一次,與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關系一樣。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司馬遷在叙述炎帝、黃帝、蚩尤三者之間的關系時,他的政治傾向性十分明顯:以黃帝為正統,在叙事時始終以黃帝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筆法。你看,言炎帝,則稱其“侵陵諸侯”,言蚩尤,則稱其“作亂,不用帝命”,而且是“最為暴”,特别是司馬遷前面說“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後面又說,在這樣的敏感時期,“軒轅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無德,炎帝失德。司馬遷更本就沒有以炎帝為本位來紀事。既然已經在做了這樣的鋪墊,司馬遷為什麼還要諱言黃帝啥蚩尤呢?沒有必要,事實上,司馬遷并沒有諱言黃帝殺蚩尤,你看,他不是說黃帝“遂禽殺蚩尤”嗎?既然如此,我認為,說司馬遷為避免軒轅黃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識的将本為同一個人的炎帝、蚩尤分為兩個人來叙述是沒有道理的。
那麼,怎樣來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間的關系才比較合适呢?我覺得這個答案可以這樣來寫: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時期的兩個主要首領,蚩尤曾一度驅逐炎帝榆罔自立為炎帝,這是涿鹿之戰發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人生的路,自己去走,
别人的嘴,随便他說,
我們不需要讨好每一個人,
隻要盡心盡力做事,本本分分做人,
即使沒人喜歡,也要過得精彩,
就算沒人欣賞,也要活得漂亮!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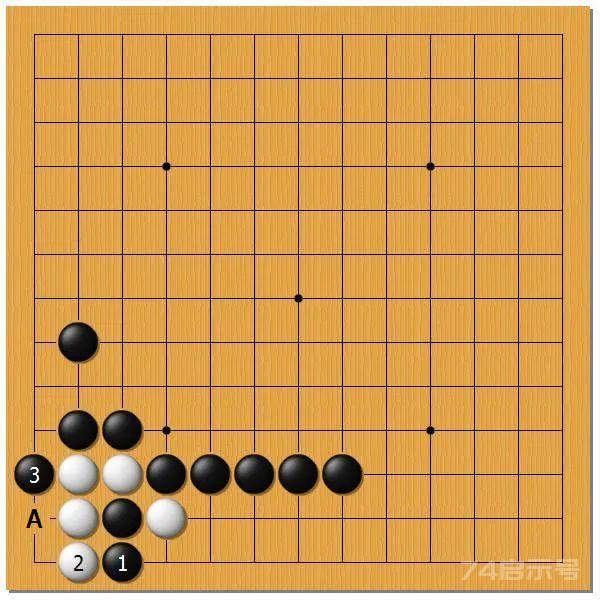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