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老舍:我怎樣寫《駱駝祥子》
- 文化
- 7個月前
- 103
( the parts into and as on this blog.TKS)
從何月何日起,我開始寫《駱駝祥子》?已經想不起來了。我的抗戰前的日記已随同我的書籍全在濟南失落,此事恐永無對證矣。
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系。在寫它以前,我總是以教書為正職,寫作為副業,從《老張的哲學》起到《牛天賜傳》止,一直是如此。這就是說,在學校開課的時候,我便專心教書,等到學校放寒暑假,我才從事寫作。我不甚滿意這個辦法。因為它使我既不能專心一志的寫作,而又終年無一日休息,有損于健康。在我從國外回到北平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去作職業寫家的心意;經好友們的諄諄勸告,我才就了齊魯大學的教職。在齊大辭職後,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沒有作職業寫家的可能。那時候,正是“一二八”以後,書業不景氣,文藝刊物很少,滬上的朋友告訴我不要冒險。于是,我就接了山東大學的聘書。我不喜歡教書,一來是我沒有淵博的學識,時時感到不安;二來是即使我能勝任,教書也不能給我象寫作那樣的愉快。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獨斷獨行的丢掉了月間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裡一時一刻也沒忘掉嘗一嘗職業寫家的滋味。
事有湊巧,在“山大”教過兩年書之後,學校鬧了風潮,我便随着許多位同事辭了職。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風向,也沒同任何人商議,便決定在青島住下去,專憑寫作的收入過日子。這是“七七”抗戰的前一年。《駱駝祥子》是我作職業寫家的第一炮。這一炮要放響了,我就可以放膽的作下去,每年預計着可以寫出兩部長篇小說來。不幸這一炮若是不過火,我便隻好再去教書,也許因為掃興而完全放棄了寫作。所以我說,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系。
記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閑談,随便的談到他在北平時曾用過一個車夫。這個車夫自己買了車,又賣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還是受窮。聽了這幾句簡單的叙述,我當時就說:“這頗可以寫一篇小說。”緊跟着,朋友又說:有一個車夫被軍隊抓了去,哪知道,轉禍為福,他乘着軍隊移動之際,偷偷的牽回三匹駱駝回來。這兩個車夫都姓什麼?哪裡的人?我都沒問過。我隻記住了車夫與駱駝。這便是駱駝祥子的故事的核心。從春到夏,我心裡老在盤算,怎樣把那一點簡單的故事擴大,成為一篇十多萬字的小說。
不管用得着與否?我首先向齊鐵恨先生打聽駱駝的生活習慣。齊先生生長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許多家養駱駝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來,我須以車夫為主,駱駝不過是一點陪襯,因為假若以駱駝為主,恐怕我就須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與駱駝的情景了。若以車夫為主呢,我就無須到口外去,而随時随處可以觀察。這樣,我便把駱駝與祥子結合到一處,而駱駝隻負引出祥子的責任。
怎麼寫祥子呢?我先細想車夫有多少種,好給他一個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餘的各種車夫順手兒叙述出來;以他為主,以他們為賓,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會環境,他就可以活起來了。換言之,我的眼一時一刻也不離開祥子;寫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車夫們而外,我又去想,祥子應該租賃哪一車主的車,和拉過什麼樣的人。這樣,我便把他的車夫社會擴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紹進來。可是,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還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裡,我決定不許任何人奪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難想到的。人既以祥子為主,事情當然也以拉車為主。隻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車發生關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樹下那樣。
可是,人與人,事與事,雖以車為聯系,我還感覺着不易寫出車夫的全部生活來。于是,我還再去想:刮風雲,車夫怎樣?下雨天,車夫怎樣?假若我能把這些細瑣的遭遇寫出來,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為一個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連一陣風,一場雨,也給他的神經以無情的苦刑。
由這裡,我又想到,一個車夫也應當和别人一樣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問題。他也必定有志願,有性欲,有家庭和兒女。對這些問題,他怎樣解決呢?他是否能解決呢?這樣一想,我所聽來的簡單的故事便馬上變成了一個社會那麼大。我所要觀察的不僅是車夫的一點點的浮現在衣冠上的、表現在言語與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車夫的内心狀态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麼樣子。車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與生命上的根據。我必須找到這個根源,才能寫出個勞苦社會。
由一九三六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與相貌變換過不知多少次——材料變了,人也就随着變。
到了夏天,我辭去了“山大”的教職,開始把祥子寫在紙上。因為醞釀的時期相當的長,搜集的材料相當的多,拿起筆來的時候我并沒感到多少阻礙。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開始在《宇宙風》①上出現,作為長篇連載。當發表第一段的時候,全部還沒有寫完,可是通篇的故事與字數已大概的有了準譜兒,不會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沒有這個把握,我是不敢一邊寫一邊發表的。剛剛入夏,我将它寫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風》每月要兩段,連載一年之用。
當我剛剛把它寫完的時候,我就告訴了《宇宙風》的編輯: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滿意的作品。後來,刊印單行本的時候,書店即以此語嵌入廣告中。它使我滿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醞釀得相當的長久,收集的材料也相當的多,所以一落筆便準确,不蔓不枝,沒有什麼敷衍的地方。(二)我開始專以寫作為業,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寫作這一回事,所以雖然每天落在紙上的不過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筆的時候,心中并沒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時候長,筆尖上便能滴出血與淚來。(三)在這故事剛一開頭的時候,我就決定抛開幽默而正正經經的去寫。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機會,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時候,事情本沒什麼可笑之處,我也要運用俏皮的言語,勉強的使它帶上點幽默味道。這,往好裡說,足以使文字活潑有趣;往壞裡說,就往往招人讨厭。《祥子》裡沒有這個毛病。即使它還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實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裡硬擠出來的。這一決定,使我的作風略有改變,教我知道了隻要材料豐富,心中有話可說,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決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決定了文字要極平易,澄清如無波的湖水。因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闆。恰好,在這時候,好友顧石君先生供給了我許多北平口語中的字和詞。在平日,我總以為這些詞彙是有音無字的,所以往往因寫不出而割愛。現在,有了顧先生的幫助,我的筆下就豐富了許多,而可以從容調動口語,給平易的文字添上些親切,新鮮,恰當,活潑的味兒。因此,《祥子》可以朗誦。它的言語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許多缺點。使我自己最不滿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點。因為連載的關系,我必須整整齊齊的寫成二十四段;事實上,我應當多寫兩三段才能從容不迫的刹住。這,可是沒法補救了,因為我對已發表過的作品是不願再加修改的。
《祥子》的運氣不算很好:在《宇宙風》上登刊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戰。《宇宙風》何時在滬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過沒有。後來,《宇宙風》社遷到廣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單行本。可是,據說剛剛印好,廣州就淪陷了,《祥子》便落在敵人的手中。《宇宙風》又遷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的機會,但因郵遞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見到它。後來,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紙型買過來,它才在大後方稍稍活動開。
近來,《祥子》好象轉了運,據友人報告,它已被譯成俄文、日文與英文。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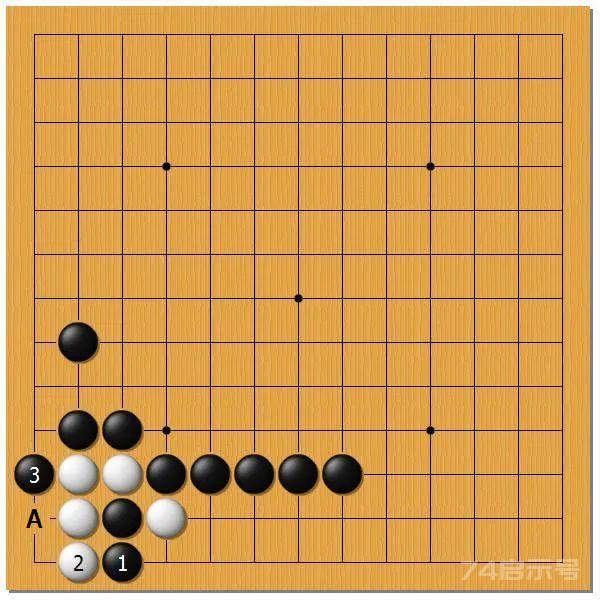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