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說中肯的話,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
- 文化
- 2年前
- 242
.
書邊小劄
穆濤會說“五句話”
北京日報 |2022年11月25日
蕭躍華
穆濤的《先前的風氣》,鈎沉稽古,發微抉隐,談及如何繼承和發揚先秦、兩漢的良好政風、民風、學風、文風,讀史講緻用,溫故為知新,寫出了“直接對應着漢代的文風”的百餘篇短文,結集出版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授獎詞稱其文将“曆史的省思、世相的洞察與思想者的話語風度熔于一爐”。
這位燕趙之士深耕三秦大地29年,熟讀先秦、兩漢經史子集,本職為《美文》執行主編。他有具體的衡文标準:“我覺着,會說五句話,差不多就是一流文章,這五句話是,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說中肯的話,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這“五句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賈平凹贊其文“今天看有意思,明天看有意思,後天看還會有意思”。
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
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即心底生出、自然而然的話,有世俗味、煙火氣、常人體溫的話。一個人活着,氣色好,有生氣,有正氣,或活得發達了,生出大氣象,形成大氣場,離不開五谷雜糧墊底。一個在家裡、在朋友間、在社會上雲山霧罩的人,是不招人待見的。一個人叙述人生的體會和感悟,用大而空那套玩意兒,聽着熱鬧,但語無歸宿,如靈魂懸浮半空,找不到承載的東西,會沒着沒落的。
西安有句土話:“聽聽哭喪的聲音,就知道了誰是閨女,誰是兒媳婦。”一個人怎麼說、說什麼,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紀曉岚《閱微草堂筆記》寫身邊事眼前事,“冷眼看世事,但心是熱的。文風也樸實,筆下全是老百姓的大實話,不扭捏文人腔,不高瞻遠矚地提升境界”(《大實話》)。世道裡有人心。“孔子的自我評價是:'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不是故意低姿态,是老僧的家常話呢。”(《世道》)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心始動人。他們的著作曆經歲月篩選流傳下來,還将繼續流傳下去。
文章還是樸素的好。穆濤寫伯樂賈平凹的《以前》,不粉飾,不矯情,不虛僞——“他嗜賭,隻是赢的時候少,手藝弱些,但經濟上不受大損失,超過一百元,手就不往兜裡掏了。他擅長賒賬,他不說賒,叫挂賬。挂得多了,我買回一個小黑闆,放他書櫃裡,每次用粉筆記上:某日欠×××元。下次再聚,他先擦了黑闆上的字,再動手洗牌。”“打牌的時候賭錢,預測的時候賭物,這是他定的潛規則。我有好幾件收藏被他抱回了家裡,其中挺心痛的一個大的石印章,石頭有齊腰高,石質沉着,淺褐顔色,尤其刻工好,刀法刻意講究,他叫了兩個人來擡,下樓的時候,我沿途護送着,見我陰沉着臉,他還嘲笑:'一個小副主編,家裡藏這麼大個印,你想奪權呀。’”讓他心疼的東西也不少。
這樣的文章真實、有趣、耐看,無損伯樂的光輝形象。
蘇東坡跋座師歐陽修書雲:“此數十紙,皆文忠公沖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穆濤其文,無論讀人的《收藏》《千字文》《另一支筆》,還是讀史的《黃帝的三十年之悟》《采風是怎麼一回事》《會說話》,皆有“沖口而出,縱手而成”的流風遺韻。
說中肯的話
說中肯的話即正中要害、扼要懇切的話,“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話,“為社會,為國家多做有益處有功德的事情”(《坐船和吃飯》)的話。穆濤的散文像雜文,文中或結尾處三言兩語,話裡有話,直抵人心,但少了魯迅的嬉笑怒罵、橫眉冷對,不知是時代變化,抑或性格使然?
穆濤認為:作家最珍貴的是特立獨行和文化良知。作家說真話是底線,寫文章要有真知灼見。作家的責任和價值,就在于找出生活“五彩缤紛”背後的真相。文學雜志應該關注社會進程,應該傾聽思想的車輪與路軌相互摩擦所發出的聲音。人世間的好文章,就是要寫透天是怎麼磨煉人的。
這麼說,也這麼幹。
他特别關注社會風氣的涵養。我們老祖宗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有大規矩的。周文王确立了以禮入教,以德治國,以人心和諧維護穩定的治國理念。董仲舒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裡的核心位置。即使再偏僻的山村,再沒念過書的人,儒家“仁義禮智信”那些基本常識也是熟稔的。不管如何改朝換代,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鄰裡往來,都有規矩。七十二行,也各有行規。四大文明古國唯我獨存,恐怕這是長壽基因之一。
穆濤充滿憂患:“我們用三十多年時間實現了經濟大進步,但這些年,中國人傳統行為裡善良淳厚的那些東西随風消逝了多少呢?”(《師和傅》)他知道社會風氣的涵養,成就甚難,進化甚緩。但如亂砍濫伐,水土流失,則如江河決口,水之就下,退化甚易。鄉下人蓋房子,是重視打地基的。舊秩序被砸爛之後,用新道德“能支撐得住廣廈千萬間嗎?”穆濤之問,多少有些賈誼《陳政事疏》“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的悲催,但心系社稷是殊途同歸的。
他特别關注中國标準的确立。世界上強大的民族,都是用本民族的思維方式思考事情和做事的。漢唐盛世,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都有自己的标準,而且是清一色“中國制造”。清王朝閉關鎖國,自取其辱,自取滅亡,一批批有識之士走向世界,學東洋,學西洋,學蘇俄,“師夷長技以制夷”。改革開放,我們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新的實踐,進行新的創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們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在解決“挨打”和“挨餓”問題後還面臨國際輿論場“挨罵”的被動局面。
穆濤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一次次呐喊:“泱泱大國,沒有自己的标準是真正可怕的。我們現如今國運昌達,經濟上是世界老二了,但這個排名标準是人家的,不止于此,金融、環境、教育乃至文學,太多的行業标準都聽命于人,這真是值得思量再思量的事。”(《活力源》)他一次次疾呼:“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領域,有點類似當下的汽車制造業,整條生産線,包括發動機都是進口的,國産貨不具規模,多項指标也不過關……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是給文學定标準、立規矩的,中國文學的根,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中國人的精氣神。裁剪唐裝,用量西裝的尺子不一定合适。”(《文學标準和文學生态》)穆濤深知大學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學領域,關乎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根本。強大的文化是強大國家之本,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态占不了上風,不太可能實現大國夢。他秉承傳統文章警世道、醒人心的文風,力所能及地在文壇發表自己的看法,洋溢着清正之氣、赤子情懷。
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
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即說自己的話,說讀者豎大拇哥的話,說聽衆自發鼓掌的話。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有見地有分量最要緊。個性和水平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共同提高。
穆濤擅長說文解字。試舉三例:“儒”這個字的結構,一邊是人,一邊是需,内涵有兩層意思,一是自己需要,再是被旁人需要;“氣”這個字,繁體的寫法是“氣”,下邊有個米字底,一個人的氣象是要有米谷做基礎的;“道”這個字,頭在上,腿腳在下,思想與踐行融為一體,空想,瞎琢磨,或本本主義,唱高調都不是道。《匠》《靜雅》《秩序》《清談和清議》……穆濤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通過解字釋詞生發議論,沒有學究氣,也不掉書袋,令人恍然大悟、茅塞頓開。
穆濤擅長今古對照。他寫漢代養殖大戶蔔式兩次捐資武帝北伐、南征,當上了京官,後因妄議車船稅,名噪一時的愛國擁軍模範改任閑職去了;說雍正也搞形式主義,明知當時辦案刑訊逼供是常态,手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方針,诏令衙門張挂萬事大吉。《劉邦的新農村建設》《事關唐朝的三個問題》《官職》……如此一喻,原本闆着臉孔,缺情少趣的曆史活蹦亂跳起來了。
穆濤擅長言人之所未言,抄錄兩段,附骥議論以飨讀者:
《去欲的态度》:“一個人活到六七十歲,把人生的基本東西看透了,但活明白了就退休了,隻好把'人生經驗’傳遞給下一代。這個節骨眼上,老天爺又加裝了一個'代溝’的裝置,孩子不吃老子那一套,所有的事情要重新來過,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人生的跟鬥再重新跌一圈。”杜牧《阿房宮賦》的豹尾最有嚼頭:“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地“再重新跌一圈”和“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過程。
《曆史的學名叫“春秋”》:“中國的皇帝,因為是家庭承包制,業務水平差别比較大,像抛物線,高和低的落差很懸殊。但中國的宰相們,基本保持在一條相對高的水準線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别在業務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别不在業務能力,而是心态、心地和心術。”政治裡的好和劣是複雜的,心态、心地、心術更複雜。北宋新黨、舊黨之争,曆經三代皇帝也未能平息朝廷惡鬥。王安石為相,對舊黨趕盡殺絕;司馬光為相,對新黨趕盡殺絕,甚至對提不同意見的“難友”蘇東坡也忍下手。皇帝、宰相如此,北宋國運可知。“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複。”這大概是曆史的可怕之處、魅力之處吧!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口舌之徒可争。“誇一個作家,最了不起的'授獎辭’,是說他'得風氣之先’或'開一代文風’,意思是說他和這個時代的文風不太一緻。”(《讀文件》)如果散文界多些這樣風格的作家,是文學之福。.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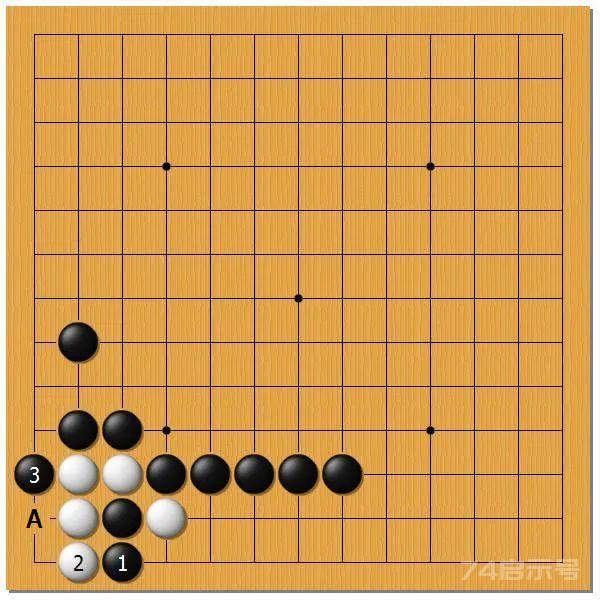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