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将會徹底改變電影藝術
- 娛樂
- 3年前
- 352
作者:Wheeler Winston Dixon
譯者:陳思航
校對:Issac
來源:Senses of Cinema
我們也曾見過這樣的場景,但卻是在電影之中:一場神秘的、無法治愈的瘟疫,突然不知道從哪裡冒了出來,然後便肆虐了全球。
前有英格瑪·伯格曼的《第七封印》(1957),後有史蒂文·索德伯格的《傳染病》(2011)——前者诠釋了十四世紀的黑死病,而在後者之中,一種神秘的病毒在數天之内導緻了無數痛苦的死亡,整個社會對于它的降臨毫無準備,繞着徒勞的圈子,試圖遏制疾病的傳播。
《第七封印》
然而,這一次,銀幕式的奇觀與觀衆之間不存在任何隔閡。這一次,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就如銀幕上反複呈現的流行病慘狀那樣,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準備。
《傳染病》
唯一接近這種全球影響力的,或許隻有1918年到1920年那場所謂的「西班牙」流感。那次疫情感染了全世界的5億人口,死亡人數在1700萬到1億之間——這一事件的數據至今仍不準确——并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進程。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人吸取教訓,世界各國的政府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
2019年年末爆發的COVID-19病毒已經蔓延到了全球,截至2020年3月25日,每1000名感染者的死亡率為4.5%。而且,這種病毒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
沒有疫苗、沒有治愈方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患者與社會上的其他人隔離開來,就像在黑死病期間所做的那樣。接下來,COVID-19的患者必須自己戰鬥,老年人特别容易病重、死亡。這是一個完美的恐怖電影場景,但不幸的是,這是一個我們無法醒來的噩夢。
當然,在這樣的時刻,人們卻被迫适應新常态,他們不知道這場大流行何時會結束。當我在2020年3月下旬寫下這篇文章時,我希望8月底情況會有所緩解。
但現在最好的消息是,COVID-19将會繼續存在,這是一種常年的季節性疾病,在找到疫苗之前,它将繼續扮演一位緻命殺手。
那麼,我們該如何應對它呢?我們想去看電影,但是電影院關門了,而且它們有充分的理由。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公共場所都已經被關閉(至少開放時間被大大削減),在大多數情況下,經過許可的聚衆人數是10人以下,最嚴厲的政權還強制實施了屋内隔離。
商店、音樂廳、教堂、婚禮、葬禮、一切公共集會——一切都将成為曆史。如今,隻要看着人們走在紐約市街頭的照片,我們的心中就會升起一種懷舊之情。
一切都轉移到了線上。我們都看過那些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意大利、中國和西班牙)的視頻,他們在陽台上相互唱歌,這都是為了保持「社交距離」——這四個字是新時代的流行語。
世界各地的電視和電影制作都已經停止,幾乎所有院線電影的上映日期,都被推遲到了影院可以重新開放的時刻——但那究竟是什麼時刻?
任何試圖計劃、管理COVID-19病毒時間表的嘗試都是徒勞的,創造時間表的是病毒,而不是我們。我們能做的隻有洗手、保持我們和他人的距離、呆在家裡,直到危機過去——祈禱危機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過去。
那麼,在影院關閉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将主流電影推向付費的公衆?
環球影業決定将他們目前在映的四部影片以流媒體視頻的形式上映,它們包括奧特姆·代·懷爾德的《艾瑪》、克雷格·卓貝的《狩獵》以及雷·沃納爾的《隐形人》。
《艾瑪》(2020)
這些影片的網播票價均為二十美元,不過這場實驗可以說是收獲了慘敗:人們習慣為一部最近的影片支付2.99美元或是3.99美元,而且上述的所有電影都是相對低成本的項目,不在影院上映就可以收回制作成本。
如果我們想看到那些大片,那些傳統上會在周末的影院舉行大規模首映的巨制,那麼我們就必須繼續等待了。但是,觀衆會重返影院嗎?最近,影院的老闆們一直在讨論這個問題,為了讓觀衆重返影院,他們可能會讓觀衆免費入場,直到他們再次養成看電影的「習慣」。
《狩獵》 (2020)
在線影像的世界變得空前繁榮,以至于流媒體巨頭自願将畫質從高清降低為标準,以此清理出額外的帶寬,以供大批新的在線客戶使用。
當然,網飛已經實現了飛躍式發展,Hulu、Amazon Prime和其他流媒體視頻來源同樣如此。而且,随着傳統的實體店紛紛關門,人們隻能在線訂購商品、選擇服務。
整個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彼此隔絕的社群,人們完全通過Zoom、Facebook和FaceTime生活。這一切都是因為,面對面的接觸現在已經變得如此危險。
在紐約,通常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已經空無一人。 洛杉矶、倫敦、布裡斯班、惠靈頓,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城市(甚至是小鎮)均是如此。
如果非要說的話,COVID-19帶來了某種奇怪的好處——個體藝術家開始全面回歸DIY的電影與視頻制作,他們會上傳完全由個人創作的影像,或是一些過去的作品,我們如今似乎已經很難體認任何「過去」了。
與此同時,非法上傳到網絡上的經典電影的數量也大幅增加。隻要你能找到合适的渠道,整個二十世紀的全球電影都是在線、免費的。
而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幾個月内。然而,我們對它們的看法,以及我們思想的變化,似乎是不可逆的、長期的。如今,全球各地的深夜脫口秀節目,都依賴Skype訪談來提供節目内容。
航空公司紛紛關門,機場紛紛關閉,連鎖酒店裡有着數千個空房間,因為沒有人想坐飛機——實際上,也沒有人可以自由地坐飛機,因為幾乎每個國家都對旅行者實施了某種禁令,試圖遏制病毒的發展。
這一切何時會結束,我們不得而知。事實上,除非我們創造出一種廉價的、具有普遍性的治療方案,除非我們治好那些已經感染的人,否則我們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結束。
大多數專家認為,任何有效預防措施的出現,都至少需要花費一年或更長的時間——盡管疫苗的試驗已經開始了。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考慮的是,我們對于全球性破壞的迷戀,究竟如何導緻了我們的自滿。有些事隻能在電影中發生,我們無法在現實中承受它們。
「一場全球性的緻命流行病」——這一主題在電影中有着許多的變體,它似乎總能受到觀衆們的歡迎,它們想要虛構的危機帶來的風險與刺激,但同時又想要與之保持安全的距離,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永遠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為威廉·卡梅倫·孟席斯導演的《笃定發生》(1936)撰寫劇本時,他準确地預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同時他也預測到了一些當時沒有發生的事情:
一場名為「漫遊症」的世界性瘟疫,導緻人們像僵屍一樣漫無目的、搖搖晃晃地遊來蕩去,感染所到之處的其他人,強制處死——通常用的是槍殺的方式——是阻止他們攻擊的唯一途徑。
《笃定發生》
無論是在烏巴爾多·拉格那和西德尼·薩爾科夫的《地球最後一人》(1964)中,還是在鮑裡斯·薩加爾的《最後一個人》(1971)和弗朗西斯·勞倫斯的《我是傳奇》(2007)中,病毒導緻的瘟疫都以相似的方式摧毀了文明,最終隻剩下幾個幸存者,與受感染的行屍走肉們進行着鬥争。
《 地球最後一人》 (1964)
特倫斯·費舍爾的《地球在尖叫聲中毀滅》(1964)假定了一場「毒氣襲擊」,造成了除少數幸存者之外所有人的死亡。
人們都被迫呆在受管控的通風區域或是氧氣帳篷之中,這是讓他們繼續活下去的方式。
在羅伯特·懷斯的《人間大浩劫》(1971)中,科學家們紛紛前去對抗一種來自太空的、可以在空氣中傳播的病毒,這種病毒能在幾秒鐘之内殺死所有被它觸及的生命。
《人間大浩劫》(1971)
在約翰·斯特奇斯的《最機密第三站》(1965)中,一種在美國沙漠的生化武器實驗室秘密研發出來的緻命病毒,被一個一心想要毀滅世界的狂熱分子竊取。
在金成洙導演的、近期的韓國電影《流感》(2013)中,H5-N1流感病毒的爆發,在36小時内殺死了所有的感染者,而這份名單仍在不斷延長。
《流感》
但是,或許最為有效的比較,應該是羅傑·科曼那部1964年的《紅死病》,這部影片是根據埃德加·愛倫·坡的幾個故事改編的,它的攝影師是才華橫溢的尼古拉斯·羅伊格(後來也成了導演)。
這部影片與《第七封印》顯然有相似之處,但它也有一些獨屬于自己的優點。這部作品講述了信仰撒旦教的王子普羅斯佩羅(文森特·普萊斯飾)在中世紀的意大利小城成為放蕩統治者的故事。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因為紅死病的影響,死在了普羅斯佩羅那座城堡的牆外。
《紅死病》
與此同時,他帶領着一群疲憊的貴族狂歡着、施行着一系列虐待狂式的遊戲。但是,這最終導緻了所有派對參與者的死亡,因為紅死病進入了城堡,它先是擊倒了一個人,然後擊倒了所有人。
COVID-19病毒确實成為了某種偉大的均衡器。沒有人能夠幸免于難。而且,它看起來似乎像是一種頑強的、多年生的植物,最終将會加入那些常規疾病的行列,正因如此,它的出現顯得格外令人擔憂。然而,從電影誕生的那天開始,從我們第一次因為銀幕而思考「不可避免的死亡」時,我們就一直在為它「作準備」。
如今,這種威脅不再是抽象的,它成為了一種真實。當我們将生活遷移到網絡上時,當我們需要獲取商品、服務、娛樂和社交時,我們會日益将現實世界抛在腦後。 《第七封印》
當我們在銀幕上創造的虛構影像成為現實的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個半永久的隔離世界。我們如今制作的影像,隻能與遙遠的過去建立一種幽靈般的聯結。
當這種病毒最終被征服的時候,它将在文明上留下永遠無法磨滅的印記。
在危機過去之後,我們将會創造一種什麼樣的電影呢?就像9/11一樣,COVID-19改變了所有的規則。我們在未來創造的東西,将與過去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你可能想看:

![[書法]閑暇草書彙03](https://m.74hao.com/zb_users/upload/2024/10/202410161729086639361289.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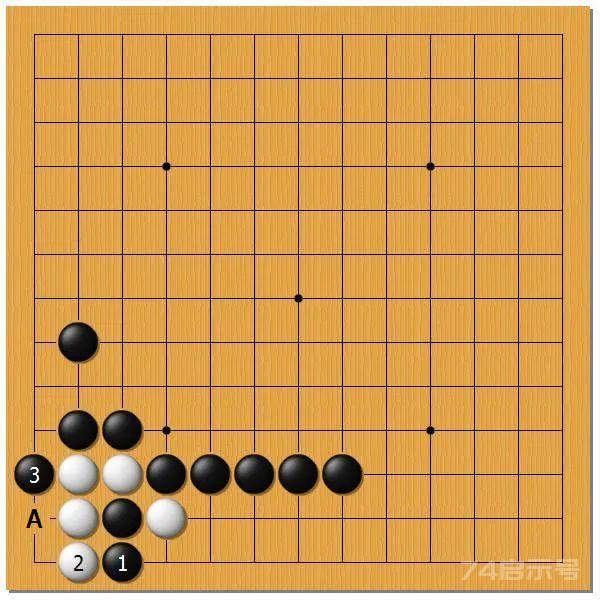







有話要說...